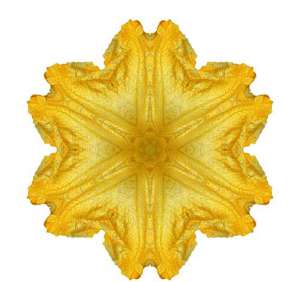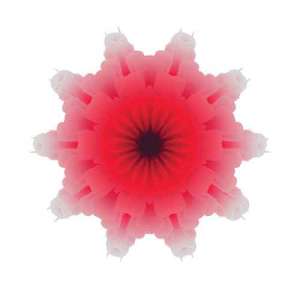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发布时间:2019-11-02 10:01:15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一、导 言
前辈学者曾经倡导:做学问需要从不疑处生疑。什么叫“不疑处”?我的理解,就是一般以为“当然如此”的问题。因为“当然如此”,无人去深究,人们自然对它“不疑”。不仅不疑,有时甚至像对待几何公理那样,把它作为推导、证明其他问题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发展史考察,很多问题都是从人们以为“当然如此”的地方,也就是从不疑处生发出来的。
就佛教而言,曾长期存在这样两个人们以为当然如此的问题:
第一,就中国佛教而言,古代很多人认为,中国佛教徒应该学习纯正、正统的印度佛教并在传播中努力保持印度佛教的纯正性。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过是泾水、渭水的关系。泾水、渭水虽然合流,但依然泾渭分明。
第二,就印度佛教而言,人们把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与发展,完全看作是印度文化本身的自我逻辑演化。一旦发现在佛教典籍中有其他文化的因子,他们就主张:这些内容不属于佛教,这些经典是伪经。
上述两点,成为很多人看待佛教的思维模式。在我接触的范围内,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论证过上述两个思维模式的合理性,但人们一直把它们作为“当然如此”的事实,作为思考其他问题的基础。佛教内部如此,佛教外部也是如此。
就上述前一个模式而言,佛教传入中国,儒教、道教很多人攻击它是夷教,反对以夷变夏。南北朝三教论衡,夷夏论是个大题目。唐代韩愈依然拿它做文章。直到宋代以下,我们有时还能从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听到这种声音,这说明了儒家思想的僵化。我在《佛教志》[1]一书中曾有简要分析,此不赘述。
近代以来,通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人们发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实际上始终在接收中国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乃至最终由印度佛教逐渐演化为中国佛教。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佛教的中国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佛教中国化的讨论十分兴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基本思维模式中的前一个模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但后一个模式,即“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完全是印度文化本身的自我逻辑演化”,至今还没有被动摇。“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提出,就是对后一个模式的挑战。
所谓“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是指由于文化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因此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随着佛教传到整个亚洲,在影响亚洲文化面貌的同时,它本身也受到整个亚洲文化的滋养。可以说佛教的产生固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现象是涉及佛教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当时写了《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1),做了一些资料的准备。2005年正式写了《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与《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两篇文章,分别在海峡两岸及日本发表(2)。在上述文章中,我以《净度三昧经》等经典为例,说明在佛教发展中存在着文化汇流现象并初步分析了文化汇流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与方式。在此拟拓展这一论题的背景,提出新的证据,以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相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将能更加清楚地描绘出古代佛教是怎样在亚洲各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发展的。
二、从文化传播看佛典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典也随之传入(3)。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宗教的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用这一观点来考察,则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佛教这一特定的宗教体系,从它的原产地南亚印度文化圈向东亚中国文化圈传播的过程(4)。宗教是一种依托于某一特定人群的思想文化形态,它与丝绸、瓷器之类有形的物质文明有很大的不同。丝绸、瓷器等物品能够从中国向外传播,主要是它们具备了某些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生活所需的具体功用。当然,中国的丝绸、瓷器也凝结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也起到传播中华文明的作用,但那些文化元素是具象的,依托在丝绸、瓷器等具体的物品上。宗教的功用则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5),其构成则表现为一系列特有的范畴与独特的范畴组合,由此形成该宗教的理论与践行。这些理论与践行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某一特定文化圈中形成的某一宗教,它的各种范畴具有浓厚的特定文化圈的色彩;第二,这些范畴的组合方式,服从于该特定文化圈人们的思维模式;第三,宗教理论与践行的传播,需要依托特定的人群。一般情况下,这一人群就是该宗教所依托的人群。
由此,佛教传入中国,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在印度文化圈产生的组成佛教的理论与践行的特有范畴及范畴组合转变成中国文化圈能够接受的形态。这一任务由来华的佛教徒承担,转变的具体方式就是翻译。
三、格义——两种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初期来华的外国佛教徒,我想也许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隔膜,对他们来说,由于不通华语,不了解中国文化,无法独立完成翻译佛教典籍的任务,只能通过担任传译的中国人来翻译佛典、传播佛教,但初期那些担任传译的中国人刚刚接触佛教,不可能真正了解佛教。在这种近乎双盲的情况下,佛教大概只能以依附或攀缘中国的某种相近学说的面貌出现。
一类人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虽然他们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主动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于是产生所谓“格义”。
上面是从佛教初传时佛教方面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来分析格义产生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主客位文化的角度,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思考格义产生的原因。
当时,中国文化是主体(主位文化),佛教文化是客体(客位文化)。佛教文化在中国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这一主位文化如何认识佛教这一客位文化。我们知道,主体阅读客体时,往往会出现坚持本位立场、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为我所用的现象。这也是佛教初传时产生格义的原因之一。
由此,格义实际是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交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根据目前资料,“格义”这个名词是东晋竺法雅提出来的,据《高僧传》卷4:
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谘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6)
竺法雅的“格义”,指“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所谓“经中事数”,即佛经中的法数,如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之类;所谓“拟配外书”,就是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概念匹配比拟佛教法数,比如用仁、义、礼、智、信来比拟佛教的五戒。竺法雅企图用“格义”这种方法帮助初学者增进对佛经的理解。
竺法雅的格义摄意较窄,只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但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这种方法,从佛教初传起,便一直活跃在佛典的翻译与学习中。比如《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说:“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2]这是批评三国支谦、西晋竺法护等前代佛教翻译家的翻译多有格义现象。《高僧传》卷5称道安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2]355这是批评前此的佛教徒在学习中因采用格义而误解佛典原意。也就是说,“格义”可以分为狭义的格义与广义的格义。狭义的格义一词由竺法雅提出,具有特定的含义,即“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广义的格义,即“用中国传统概念比附印度佛教范畴”早就产生,广泛使用,且一直延续到后代。陈寅恪指出:
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的理学,皆格义之流。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的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的变相。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它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在我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作记叙。[3]
陈寅恪的这段话既指出格义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又谈到后人如何利用格义发展理论。也就是说,广义格义的运用在两个不同民族思想的交流中已经远远超出“初次混合品”这一初级阶段,有着更深、更广的意义。
虽然“格义”是个佛教命题,虽然陈寅恪也是在论述佛教时把格义称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但我认为,任何特殊事物中都蕴含着一般规律。实际上,直到近现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依然经常可以看到作为“初次混合品”的格义的影子。因此,广义的格义是两种文化交流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
全面论述广义的格义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大,非本文所能。即使在中国佛教史上,广义格义的产生与发展也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故以下仅拟谈谈格义在古代佛典翻译中的表现,诸如无意的误解、有意的附会、特意的曲解等,作为论述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背景描述。
四、格义与佛典翻译
佛典翻译是把佛教理论体系从印度文化圈搬移到中国文化圈的主要方式。佛典翻译不仅要解决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表述习惯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不同文化的概念范畴、思维模式的差异。解决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已经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所以道安有翻译佛典“五失本”之叹(7)。事实上,相对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思维模式而言,解决语言文字及表述习惯的差异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已。
如前所述,佛教的理论体系由各种范畴有机构成,这些范畴往往有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如果考察这些范畴与中国文化圈中有关范畴的关系,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三种情况(8):
第一,中国文化圈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范畴,比如“人”。
第二,中国文化圈有大体相近的范畴,但意义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比如“地狱”、“天”。
第三,中国文化圈中根本没有这种范畴,比如“轮回转世”、“泥洹”。
翻译时,如果遇到第一种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如果遇到第三种情况,我相信虽然翻译者会感到非常困难,但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人们终于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名词,诸如意译名词“轮回转世”、“解脱”;音译名词“佛”、“泥洹”;音译、意译相结合的名词“舍梨子”来对译这些中国文化圈原本没有的范畴。恰恰在第二种情况下,最容易望文生义,亦即产生格义,从而引起似是而非的理解。也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很难发现自己的翻译与印度文化圈的原意已经发生偏移,用自己的翻译名词去理解佛教,甚至以为“当然如此”。
五、“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象
我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往往发现汉译佛经中会出现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佛经原本在印度文化圈中产生,不应该出现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会进入汉译佛经,我以为这是佛经翻译过程中,遇到上述第二种情况,翻译者采用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对译与该范畴意义相近的印度文化圈范畴,从而产生上述现象。这里举一个例子:
《中阿含经》卷35记载摩揭陀国未生怨鞞陀提子(即阿阇世王)想要攻打跋耆国,派大臣前往鹫岩山(即灵鹫山)咨询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只要跋耆国人坚持执行“七不衰法”,那么跋耆国就是不可战胜的。所谓“七不衰法”,实际是七条行为规则或道德规范。在《长阿含经》卷2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行文虽然比《中阿含经》顺畅文雅,但对“七不衰法”的翻译却有不同。这里将两者的不同罗列如下(表1;为便于比较,表中对《长阿含经》卷2中“七不衰法”的先后次序有所变动,可参见笔者所加的序号)(9)。
表 1
从《中阿含经》第1-2条可以看出,这个跋耆国与释迦牟尼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一样,都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若有大事,部落成员集体开会,商议决定,但《长阿含经》的翻译却把印度原始社会的平等会商制度,表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和顺,上下相敬”。
《中阿含经》第3条讲的是跋耆国人坚持传统,不加变动,但《长阿含经》卷2翻译为“不违礼度”。“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法则。
《中阿含经》第4条讲的是不强暴妇女,这是对男人的道德要求。《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变成对女人的贞洁指标。要求妇女守贞,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道德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阿含经》第5条讲的是尊重、供养贤人,听从他们的教导。《长阿含经》相应的条目翻译为“孝事父母,敬顺师长”,这一翻译,与原意相差甚远。
《中阿含经》第6条讲修寺供神,但《长阿含经》卷2相应的条目加入了“宗庙”这一中国元素。
第7条评述从略。
日本中村元曾经将上述两种翻译与南传巴利语佛典进行比较,指出《中阿含经》卷35的翻译比较忠实原意,而《长阿含经》卷2则大幅度偏离了原典。很显然,这是翻译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用中国传统文化去理解印度佛典,从而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印度佛典的原意。这样翻译出来的印度佛教经典,已经渗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把翻译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
六、略谈汉译佛典中的“孝”
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道德纲目。佛教初传时,中国正属两汉、西晋。当时,孝在所有道德纲目中最为重要,有所谓“以孝治天下”的说法。中国的这一现实环境,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汉译佛典。
佛教讲报四恩,具体是哪四恩,不同典籍说法不同,但均有“父母恩”。我曾经指出:
印度佛教根本没有‘孝’这一词汇,而采用“报恩”这一说法。佛教认为,释迦牟尼在无始以来的轮回转世中,曾无数次地当过各个众生的父母,也曾无数次地当过各个众生的子女。因此,释迦牟尼并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对象而报恩。他要普度众生,这也就是最大的报恩。也就是说,佛教是联系轮回来看待亲子关系的,这就使它的“报恩观”与中国的“孝道观”出现很大的差异。[4]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容不得它不讲孝。早期的三教论衡,“孝”为儒、道两教攻击佛教的一大题目,佛教不得不做出回应,如庐山慧远,著文申明佛教与中国的孝道并无悖逆,相反,它不但符合孝道,而且是超越中国的孝道的更大的孝。企图以此消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实质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佛教。正因为如此,原本宣传破除吝啬,宣传斋僧可以免除地狱之苦的《盂兰盆经》,在中国发展为宣传孝道的经典,进而发展出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变文及大本目连戏。这都是中国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改造的具体表现。
汉译佛典中出现“孝”,同样是中国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改造的方式之一。印度佛教典籍中所谓报“七世父母恩”,其“七世父母”,指的是当事人在七次轮回中所遇到的父母。这“七世父母”,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六道中的任何一类有情,但中国人往往把“七世父母”理解为血统上的七代祖先,诸如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之类(10)。
有研究者对我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方广锠先生在《佛教典籍百问》中说,印度佛教没有“孝”这个词汇,只有“报恩”的说法,而且不以某个特定的众生为报恩对象。无独有偶,耿敬在《佛教忠孝观的儒家化演变》中也说“原始印度佛教在忠孝观上与中国儒家忠孝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印度,佛教并不特别注重孝顺思想的宣扬,只是从佛教的报恩思想出发,才在一些后世佛经中引发出孝顺亲者的主张”。从他们的话来看,似乎佛教最初是没有“孝道”这一词汇的,只是后世传至中土时,为了适应国情,才从原有的报恩思想引申出“孝”这种理论。
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原始佛教由于缘起和轮回思想的影响,对孝道不是很关注也许是事实,但要说没有“孝”这个词汇,未免有失偏颇。其实,在最早传入中国的《四十二章经说》中就有“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而在《佛说梵网经》中更明确出现了“孝道”这一词语,“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加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加报。杀生报生,不顺孝道”。
…………
佛教戒律更是针对这种不孝顺的人专门制定了具体的戒条以示惩罚。
《五分律·卷二十》说:“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佛说梵网经》还规定了几种关于不孝的“轻垢罪”:佛的弟子,应常发“孝顺父母师僧”之愿,若“一切菩萨不发是愿者,犯轻垢罪”;“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也犯轻垢罪……[5]
文章引用汉译佛经,企图证明印度佛教也有“孝”这个词汇。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做文献学的溯源考察,不了解汉译佛典中的这些“孝”,都是翻译中文化反浸的产物,立论也就无法成立。因此,说印度佛教有“孝”这个词汇,不能从汉译佛经中去寻找证据,而要到印度的原典中去寻找。其实,不仅印度佛教没有“孝”的观点,整个印度文化都联系轮回转世观察亲子关系,没有与中国的“孝”相同的伦理规范,也没有一个能够与中国的“孝”完全对应的词汇。
某些印度佛典,如《五分律》及其他印度律本确有“供养父母”一说,但是,“供养”与“孝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论语·为政》讲得很清楚:
子游问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仅仅是“供养”,养狗、养马也是养,这不能算“孝”。孝要“恭敬”,核心是“无违”(11),即以“礼”作为行为规范,遇事顺从父母的意愿。其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后代将“孝顺”连用,说明了孝的精义。
我还可以举出五戒、八戒等例子,说明“孝”是怎样被强加到早期汉译佛典中的。
按照正统的解释,五戒指: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三国吴支谦翻译的《梵摩渝经》称五戒为:
守仁不杀、知足不盗、贞洁不淫、执信不欺、尽孝不醉。[6]
前四条虽然加入“仁”、“贞”、“信”等中国的道德纲目,但与原文相比,大致不差。第五条加入的“尽孝”,则是原文中怎么也找不出来的。
吴康僧会的《六度集经》的《梵摩皇经》说转轮圣王用“五教”治理天下,这“五教”实际就是五戒:
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二者,清让不盗,损己济众。三者,贞洁不淫,不犯诸欲。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五者,奉孝不醉,行无玷污。[7]
可见把“孝”塞入五戒不是个别的行为。有意思的是还把“不饮酒”改为“不醉”,看来中国的酒文化是很难改造的,所以那些翻译家不得不作出妥协。
至于八戒,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受十善戒经》称:
如来为在家人制出家法: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者,不饮酒。六者,不坐高广大床。七者,不作倡伎乐,故往观听,不着香熏衣。八者,不过中食。应如是受持。[8]
在《六度集经》中,八戒被表述为:
一当慈恻,爱活众生。二慎无盗,富者济贫。三当执贞,清净守真。四当守信,言以佛教。五当尽孝,酒无历口。六者无卧,高床绣帐。七者晡冥,食无历口。八者香华脂泽,慎无近身;淫歌邪乐,无以秽行。[7]48-49
有趣的是,同样是《六度集经》,对第五戒的表述一为“奉孝不醉”,一为“当尽孝,酒无历口”。可见康僧会完全知道第五戒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不饮酒”,说明他对第五戒的曲解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康僧会的行为已经不能用“翻译中的文化反浸”来解释,而要用下文的“编译中的文化加工”来诠释。
七、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
按照现代标准,翻译活动可以分为翻译、编译两类。所谓翻译,指作品完全忠实于原文。所谓编译,则容许编译者在作品基本内容依然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增删润饰,甚至撮略大意。
如果拿现代的标准去观察古代,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佛典翻译情况非常复杂,很难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为避文繁,此处不讨论古代佛典翻译的各种形态,仅对编译做一个定义,以便下文的讨论。我认为:中国古代佛典的编译指编译者按照某一主题对原始资料进行剪裁、组织乃至加工,由此编纂而成的文献。编译佛典的原始资料应为域外佛典,其具体来源可能是单一的,即来自同一部域外经典;也可能是多元的,即分别采撷自不同的域外经典。按照上述定义,诸如《六度集经》、《贤愚经》、《大智度论》都属于编译。
与翻译相比,编译者在进行编译时,其创作的自由度更大。上文谈到,早期来华的佛教徒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较为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为了能够让佛教更加顺利地锲入中国社会,主动地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康僧会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康僧会,僧史有传,他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父亲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内)。汉末三国,交趾汉文化昌盛,佛教亦较发达,康僧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兼有中印文化的良好素养。在此看看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如何用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进行加工。
(一)孝等道德纲目
如前所述,汉末三国,中国标榜“以孝治天下”(12)。“孝”这一道德纲目,不存在于印度文化圈,然而在《六度集经》,共出现“孝”54次。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些表述:
《六度集经》卷1:“孝子丧其亲,哀恸躃踊。”[7]5
《六度集经》卷1:“违父之教,为不孝矣。”[7]5
《六度集经》卷3:“孝顺父母,敬爱九亲。”[7]11
《六度集经》卷5:“父母年耆,两目失明。睒为悲楚,言之泣涕。夜常三兴,消息寒温。至孝之行,德香熏干。”[7]24
《六度集经》卷6:“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怀十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比门有贤。”[7]37
康僧会如此推崇孝的目的,是为了将“孝”这一当时最高的道德纲目与佛教的最高目的奉佛——信仰佛教——等同起来。在睒子故事中,他反复强调“奉佛至孝”,主张这种“奉佛至孝”之德可以感天动地,乃至使国丰民康,天下太平。
除了孝以外,“仁”出现130次。此外,诸如“子孝臣忠”、“君仁臣忠”等,均为《六度集经》宣扬的正面形象。
(二)魂灵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有魂灵。人死魂灵为鬼为神,模样与生人无异。世界的本体是元气,故魂灵的本质也是元气。
印度佛教主张轮回。轮回思想乃印度的普遍观念,属于“当然如此”的问题。因此,初期佛教时期,凡与轮回有关的问题,都无人怀疑,无需讨论。外道对轮回主体问题的讨论,当时被释迦牟尼视为“戏论”。初期佛教已有“无我说”,但当时的“无我”意为“非我”,即不要把“非我之物”执着为“我”,目的是破除贪欲[9]。部派佛教时期理论开始细密,从不疑处生疑,用“诸行无常”理论统率并发展了“无我”理论。此时的“无我”指在现实世界中,一切有为法都无常迁变,人的肉体中也不可能有常一不变的“我”。这样,“无我”理论便与轮回转世理论产生矛盾:既然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人死轮回,靠什么联系前生后世?各部派对此解释不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最基本的解释以变动不居的“识”担任轮回主体。“识”的本质是一股不断迁变的意识之流,五蕴而成,因识偏盛,名之为“识”。这样便成功解释了五蕴之体如何在三世轮转,使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三法印”成为一个圆满而无矛盾的整体。
中国文化中的“魂灵”与印度佛教的“识”是两个略微相交但差距很大的范畴。康僧会为了得到中国人的认同,采用中国文化中的“魂灵”来翻译印度佛教的“识”,把它当作轮回主体。《六度集经》卷4:“魂灵变化,轮转无已。”[7]23康僧会不承认魂灵是元气,但为了与中国文化妥协,便主张魂灵与元气相合。《六度集经》卷8:
于是群臣率土黎庶,始照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7]51
(三)太山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死以后,魂灵将归太山。康僧会接过这一观念,直接将中国的太山置换为印度佛教的地狱。
《六度集经》卷1:
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7]1
《六度集经》卷5:
妄以手捶,虚以口谤。死入太山,太山之鬼拔出其舌,着于热沙,以牛耕上。又以热钉,钉其五体。求死不得。[7]30
(四)天人感应、天神荣卫
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神秘主义思想的核心。天神荣卫则是中国民间巫教的理论,其后被道教吸收。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都被康僧会吸收到《六度集经》中。
《六度集经》卷1第3则故事,叙述释迦牟尼前世为一条大鱼,为救大旱而献身肉供黎民。死后:
魂灵即感为王太子。生有上圣之明,四恩弘慈,润齐二仪。愍民困穷,言之哽咽。然国尚旱,靖心斋肃,退食绝献,顿首悔过曰:“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丧吾命惠民雨泽。”日日哀恸,犹至孝之子遭圣父之丧矣。精诚达远,即各有佛五百人来之其国界[7]2。
故事中太子的表现完全是中国帝王在遭遇自然灾害时的形象:下罪己诏、斋戒、求告上天等等。

《六度集经》卷1:“王逮臣民,相率受戒。子孝臣忠,天神荣卫。”[7]4则表述了天神荣卫的观念。
《六度集经》中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罗列。总之,中国文化元素通过佛典编译渗透到汉译佛典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前述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主要指翻译者不懂得印度佛典的真实含义,以格义的态度进行翻译,故而产生误差。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则是编译者完全明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在有关问题上的差异,比如康僧会完全知道中国的“魂灵”并非印度的“识”,故有时他也采用“识神”一词;他知道“太山”只是方便设教,有时明确用“地狱”;他知道不能用元气来解释“识”,故而含含糊糊地采用“魂灵与元气相合”这一表述以调和印度与中国的灵魂观。也就是说,康僧会完全明白他的这些说法并不符合正统的佛教教义,但为了佛教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他有意采取上述方法。《六度集经》卷4有一篇《之裸国经》,讲兄弟两人到裸人国的故事,可视为康僧会对自己行为的辩护。即他就像《之裸国经》中的弟弟那样,不得不入乡随俗,用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进行加工。
上面以《六度集经》为例,说明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其实在佛典翻译中,也存在对部分经文进行加工的现象。比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谓:
大王!未来世中,一切国王、王子、大臣,与我弟子横立记籍,设官典主大小僧统,非理役使。当知尔时,佛法不久。[10]
由于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建僧籍、立僧官的现象乃至可能性,只有中国这样集权的国家才产生这种现象,所以,近代以来一些研究者依据这一段经文,主张《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伪经。其实,该经的翻译史是清楚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不是一部翻译经典,但上述这一段经文,又的确不可能出自印度。所以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这段文字是翻译者加进去的。翻译者在翻译佛典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加入新的内容,这种现象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屡见不鲜。如竺佛念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时,就加入不少自己撰写的文字。后来被人发现,予以删除。据《出三藏记集》记载,竺佛念擅自所加内容,总计竟达4卷之多。而《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译者恰恰是自许甚高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毘昙》,非迦旃延子比也”(1)。他翻译《大智度论》,翻译到三分之一时说:照这样翻译下去,全书要达到1000卷。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繁琐的东西。于是开始改为编译。老实说,我一直怀疑,鸠摩罗什的编译,到底有多少文字是他依据原著撮略的,又有多少文字是他自己发挥的。希望将来能够发现《大智度论》的梵本,解答我的上述疑问。总之,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佛学大家,如果他在译本中加入若干自己的内容,毫不奇怪。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没有人会对鸠摩罗什的译本提出质疑。所以本节开头说,按照现代标准,翻译活动可以分为翻译、编译两类,但中国古代的佛典翻译情况非常复杂,很难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八、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与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论述的都是在域外佛典译为汉文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反向介入印度佛典这一现象。严格讲,这种现象都发生在翻译或编译过程中,但是,汉译佛典中还有一批经典,经文中也包括不少中国文化元素,但这些元素却无法用文化反浸或文化加工来解释。可以肯定地说,在译为中文之前,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已经保存在这些典籍中。在此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有些是前此已经广为人知的,有的是我发现的。
(一)《大集经·虚空目分》中的十二生肖
这是一个经常为人们援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将十二种动物与十二支配置,成为十二生肖,这是中国文化的元素。十二生肖最早产生在什么时候,还可以研究。起码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已经有清晰的阐述,而印度没有十二生肖这一习俗,说明它并非产生在印度,但是在北凉昙无谶译的《大集经·虚空目分》中,却出现十二个动物,依次为:南方蛇、马、羊,西方猴、鸡、犬,北方猪、鼠、牛,东方狮、兔、龙[11]。除了将老虎改为狮子外,《大集经·虚空目分》这十二个动物的排列顺序乃至方位,与中国的十二生肖完全相同。这种相同,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大集经·虚空等目分》中的这些内容,也无法用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或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来解释。
(二)《四天王经》的诸多问题
《四天王经》,南北朝刘宋时凉州沙门智严、宝云译。经典不长,今全文移录如下:
佛说四天王经
宋凉州沙门智严共宝云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佛告诸弟子:“慎尔心念,无受六欲。漱情去垢,无求为首。内以清净,外当尽孝。以四等心,奉养所生。晨入尊庙,稽首悔过。朝禀暮诵,思经妙义。以佛重戒,治心秽病。斋肃静处,数息禅定。反流尽源,以求道真。寿命犹电,恍惚即灭。
斋日责心、慎身、守口,诸天斋日伺人善恶。须弥山上即第二忉利天,天帝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镇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龙鬼、蜎蜚、蚑行、蠕动之类,心念、口言、身行善恶。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复下。二十九日太子复下。三十日四王复自下。四王下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其中诸天佥然俱下。
四王命曰:‘勤伺众生施行吉凶。若于斯日有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清心守斋,布施贫乏,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翫经散说,开化盲冥,孝顺二亲,奉事三尊,稽首受法,行四等心,慈育众生者,具分别之,以启帝释。’
若多修德,精进不怠,释及辅臣三十三人,佥然俱喜。释勅伺命,增寿益算。遣诸善神,营护其身,随戒多少。若持一戒,令五神护之。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营卫门户,殃疫、众邪、阴谋消灭。夜无恶梦。县官、盗贼、水火、灾变终而不害。禳祸灭怪。唯斯四等、五戒、六斋,犹如大水而灭小火,岂有不灭者乎!临其寿终,迎其魂神,上生天上七宝宫殿,无愿不得。
若有不济众生之命、秽浊盗窃、淫犯他妻、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厌祷呪诅、嫉妬恚痴、逆道不孝、违佛违法、谤比丘僧、善恶反论,有斯行者,四王以闻,帝释及诸天佥然不悦,善神不复营护之。即令日月无光,星宿失度,风雨违时,以现世人。欲其改往修来,洗心斋肃,首过三尊,四等养亲,忠于帝王,慈心谏诤,至诚无欺,反前修来。捐秽浊之操,就清净之道。
若有改邪行就正真者,帝释及四王靡不欢喜。日月即清明,星宿有常。风雨顺时,毒气消歇。天降甘露,地出泽泉。水谷滋味,食之少病。华色奕奕,寿命益长。生不更牢狱,死得上生天上。福德所愿,自然飞行。存亡自在,项有日光。食自消化,无有便利之患。身中香洁,口气苾芬。今日、月、星宿即诸天宫宅也!七宝殿堂,悬处虚空,在意所之。寿终下生侯王之家,颜容炜烨,见者心欢。逢佛值法、贤圣,相连力行,不与罪会,必得泥洹。斯皆五戒、十善、敛情摄欲、六斋使然!
拘留秦佛时,人寿六万岁,民性无为,护彼犹养己,平等无二。彼佛去世,正教衰薄。民无正行,以渐为恶。其寿日减,至于百岁。吾善逝后,民违佛教,无复孝子。伺命减算,寿日有减。天神不佑,凶疫、恶鬼日来侵害。灾怪首尾,愿与意违,非祸纵横。生罹王法之囹圄,死入地狱、饿鬼、畜生。若出为人,必为下贱。善恶追身,犹如五谷,随其所种,获其果实。亦如夜书,火灭字存。身死名灭,殃福不朽。慎护尔心、摄身、守口,五戒、十善可从得道。吾今得佛,积行所致!”
诸比丘闻经,皆大欢喜,稽首礼佛而去。
佛说四天王经[12]
这部经中的诸天伺察、善神拥护、增寿益算、二十五戒神、天人感应、斋肃首过等等,都与中国文化的元素在在相合,也是后世疑伪经《地藏菩萨十斋日》的依据。难怪日本很多学者视这部经典为中国人所撰伪经,但是,如果我们信从历代经录的记载,则这部经典应该属于翻译经典。
其实,上面涉及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元素,并非首见于《四天王经》,三国、两晋译出的不少经典,均有这些内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三)《净度三昧经》
同样是智严、宝云翻译的《净度三昧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神明听察,疏记罪福,不问尊卑。一月六奏,一岁四覆。四覆之日皆八王日。八王日者,天王案比诸天、人民、杂类之属,考校功最。有福增寿,有罪减寿夺算。
天地浩浩,黎庶无数。诸天、地狱、五道大王、司命、都录、五官、都督、四镇王、使者、承天、大将军等,春秋冬夏承天统摄,禁察非法。总持众生名藉,制命长短,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不知天地五官所记。不能自知生所从来,死至何所。不能自知命之长短。不知为五官所收录。不知豫作善求安,不知豫作功德救罪。亦不晓依附三尊,求后世救。不晓求守戒明经道士,从求度世道。如牛老败不中用,大家言:“此牛老败不中用。烦劳牧养,久已无益我家。但当早杀。可得肉食之,亦可除烦劳。”人亦如是。不奉持戒禁,亦不作功德,如牛烦劳大家甚多。不益大家,又不能自活。人依道生,道气养之。不肯奉道,亦不能自度。为五官所收,死付地狱,尽属三十王所治如是。[13]
《净度三昧经》对“五官”解释如下:
六事罪属五官。一者行五逆罪,二者行十恶,三者不行五戒,四者不敬三尊,五者不畏天禁。何谓五官。一者仙官主禁杀。二者水官主禁盗。三者铁官主禁淫。四者土官主禁两舌。五者天官主禁饮酒。犯罪属地狱。五官呼名,各自有时。好杀无慈,心口行恶,为仙官所录,命在春。好盗贪求无厌劫人,为水官所录,命在冬。好淫欲,为铁官所录,淫鬼食其不净,并饮心血,病在心肝肾头目,命在秋。好酒醉乱,仁义不行,礼教废,为天官所录,命在夏。好妄言、两舌、恶口、传舌谗人,诽谤圣道,为土官所录,命在季月。五官主人根,人根从五事生,故有五官,乃自然之王也。五官及辅臣、小王、都录、监司、廷尉、邮公、伏夜将军、五帝使者,收捕罪人录命收神。死者不同,皆依本罪,故令不同。[13]263-264
上述文字,如果从内容考察,似乎并不属于佛教,但是从南北朝该经译出,直到智升把它视作疑经,驱逐出藏经之前,它始终保存在大藏经中并被许多佛教典籍引用(14)。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认为,这体现了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如前所说,宗教的传播就其本质而言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是双向的,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的。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向西传播,影响了中亚与印度的佛教。以文化汇流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中国文化元素所以出现在翻译佛典中,是因为这些元素早就传播到狭义的西域乃至广义的西域,在当地产生影响,被当地的佛经所吸收。其后又传入中国,翻译为汉文。简而言之,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九、两条新证据

这一出口转内销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特别由于保存在印度方面的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难以描绘其细节。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提出若干证据,证明在历史上,这一过程确实存在。
(一)《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我指导的博士生伍小劼今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15),文中指出,从经文内容和经文来源上,都可以判定《大灌顶经》12卷均为中国人撰写的伪经。该经的成分主要来自道教,也有来自民间巫道的成分。经文多处抄袭此前翻译的佛经和佛教其他伪经,作者为刘宋鹿野寺沙门慧简。
有意思的是,这部《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在隋代由达摩笈多译出,名为《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1卷。到了唐代,先由玄奘译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1卷;又有义净译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2卷。
最早出现的《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无论从经录记载,还是从内容考察,都说明它是一部伪经。梁僧佑也在《出三藏记集》中言之凿凿地记载该经为慧简所撰,但隋唐两代居然可以依据该经的梵文本先后三次翻译。三次翻译的经文,行文虽然各有时代特点,但基本内容完全相同。我们对上述事实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西传到印度,被翻译为梵文(该经的梵文残片近代在西域发现,为7世纪写本),又传回中国,译为汉文。该经在印度流传时本身发生嬗演,所以不同时代传入并译出的汉文本的行文也就互有差异。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主张“不生”的佛教体系中,出现一个追求“延寿”的药师佛本身就是一个异数。仔细考察佛典中药师佛神格的形成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实际是一个主要吸收中国文化的营养而产生的佛陀。这个问题比较大,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二)《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
这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经,妄称三藏菩提流志、三藏宝思惟等于崇福寺(16)同译,实际由唐景龙元年三阶教僧人师利伪造。《开元释教录》作者智升即为西崇福寺僧人,他在《开元释教录》卷18对此经有详尽的著录。智升称:
余曾以此事亲问流志三藏。三藏云:“吾边元无梵夹,不曾翻译此经。”三藏弟子般若丘多,识量明敏,具委其事。恐时代绵远,谬滥真诠。故此指明,以诫于后。其僧师利因少斗讼,圣躬亲虑,特令还俗。岂非上天不佑,降罚斯人。又临终之时,腹大如瓮。恶征遄及,可不惧欤。[14]
智升曾经亲自调查知情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证明《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确为伪经。
根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考订,《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第二品偈颂内容与不空所译的《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内容基本相同[15]。仅《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为七言而《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为五言。为避文繁,这里截取最后一段,以作比较(表2)。
表 2
《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为不空依据梵文所译,这在圆照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及《贞元新定释教录》中均有明确记载,不容怀疑。《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出现在前,《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翻译在后。那么,我们的结论依然只有一个:《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传到西域,译为梵文,又倒传回中国,重新译为汉文(17)。
十、结 语
文化汇流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但产生在中印文化之间,也产生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众所周知,新罗元晓等高丽著名僧人,曾经对中国佛教有过重要的影响。又如我发现古代被视为疑伪经的《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后来传到高丽,演化为讲唱文学《金犊太子》,而《金犊太子》中的一些情节,又出现在清代的《三侠五义》当中[18]。这里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又是怎样影响的,的确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清理。
虽然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但文章至此已经很长。在此以我在《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前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简短的结语:
人们常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我以为,这句话有四重含义。
首先,佛教在印度产生后,历史上曾发展出部派佛教(小乘)、大乘佛教、密教等三大派系,但后来,佛教在印度衰亡,三大派系都不复存在,而在中国,却保留了承袭印度部派佛教而来的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承袭印度大乘佛教而来的汉传佛教与承袭印度密教而来的藏传佛教。在当今世界上,如此完整保留三大系佛教形态的,唯有中国。
其次,宗教的传播,就其实质而言,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而文化本来都是适应一定的时空、在一定的民族人群中产生、发展的;当它传播到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民族人群中的时候,必然会与当地的原有文化相互影响。如果我们忽略过程,只讲结果,则其结果可能有三种:外来的压倒原有的,像伊斯兰教传入中亚等地;原有的消化外来的,像开封犹太教消融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像佛教传入中国。
我以为,佛教传入中国,可视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优秀典范。在两千多年的漫长交流中,佛教滋养了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同时,佛教受到中国文化的滋养,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最终,印度佛教演化为中国佛教。就汉传佛教而言,它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文化之鼎的三大支柱之一;就藏传佛教而言,它与藏族、蒙古族等有关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成为藏族、蒙古族及有关民族地区的主流文化;南传佛教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佛教为中国文化输送了新的血液;中国文化为佛教重塑了肌体与灵魂,赋予了更顽强、更活泼的生命力。
第三,受中国文化滋养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其后在周边国家广泛流传,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这一点而言,在传入中国的三大系佛教中,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大乘佛教与汉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汉传佛教,其后在朝鲜、日本、越南等所谓“汉文化圈”国家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印度密教与藏蒙文化相结合形成的藏传佛教,曾经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至今仍在蒙古国、俄罗斯、尼泊尔、不丹等各相关国家中保持着强劲的影响。
第四,从更深层次上讲,我们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还在于中国文化,包括汉文化与藏蒙文化,在历史上对印度佛教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以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注意。
佛教是在古代印度起源,然后传遍南亚、东亚、中亚、东南亚等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但是,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既然是文化的传播形式之一,那么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由于佛教的发展并没有局限在印度一隅,而是遍布亚洲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它受到各国文化的滋养,呈现种种形态。如前所述,既影响了各国文化,也改变了自己。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佛教适应所在地文化的需要,与所在地文化相融合;也体现在佛教融摄各地的优秀文化与思想,营养自己,发展自己。举例而言,《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相当一批大乘经典的产生地其实不是在印度,而是在我国的新疆,而新疆又是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与中国文化(包括汉文化与藏文化)交汇的地方。因此,这些大乘经典实际是上述诸种文化共同培育的结果。至于印度佛教密教受中国道教的影响,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佛教的产生虽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其他地区文化的汇流。也就是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结果中,也体现在历史的过程中[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