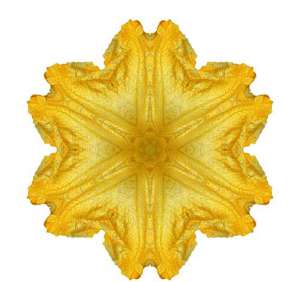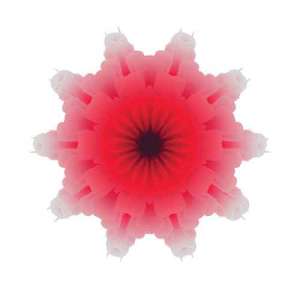印光大师讲故事之进德篇
发布时间:2019-11-10 09:54:52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印光大师讲故事 之 进德篇
去年腊月,徐某,同一川僧来报国,住多日过年,其僧袍子也未带。过年后,光呵斥之曰:“汝为僧,当于岁末年初祝国祝民。汝远出过年,袍子也不带,可知汝成年也无礼诵持念之事。幸同徐居士来,否则报国单也不持你的。”徐既由支那内学院结伴来,则徐亦是只说空话,不务实行之人。否则何肯相伴,令彼辱及于己乎?此种人,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复谢子厚居士书》
大学堂,画裸体画,以期美术进步。美术固能进步,绝不虑人道退步,畜道进步乎?——《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
光见一大老死,一人作像赞云:“于穆大雄,出现世间。”又一弟子与其师玉嵀作传云:“其行为与永明同,殆永明之后身乎?”光批云:“以凡滥圣,罪在不原。”玉师虽好,何可作如此赞叹乎?玉师有知,当痛哭流涕矣。————《致德森法师书三》
一军官,系山西繁峙县人,姓续,以国家不太平,至中山陵辟腹,被人救未死。一弟子,以彼以忧国自杀,特劝彼来苏皈依。彼寓苏多日,其妻女亦偕来过。一日领其女与仆同来,其女已有上十岁,仆有近三十岁。彼与光谈话,其女与仆戏顽。彼呵之,女不听,发气呵之,稍静一刻,又顽起来。光知彼是只知愤世,了无治世之才。只一女孩,在光处尚不受约束,况统兵乎?不能教儿女,焉能训兵士乎?——《复某居士书》
民十几年(忘其年)光到宁波,黄涵之请到道尹衙外念佛社说开示。一某大老官坐轿来,时光已演说。后说到敦伦尽分,父慈子孝等处,其人乘轿而去。然光素抱此志,不以人不喜闻而改方针。光之说法与一切法师不同。诸大法师多注重在谈玄说妙,光不会说妙,多注重在教人敦伦尽分。——《复屈文六居士书二》
光初出家至一居士家,其家俱信佛,其婆媳二人,儿女三、四个各供一佛。供佛之棹,系一长棹,媳烧香供水掸灰,只在己佛前,婆之佛棹灰也不掸。光见之心痛,以为此种人,未闻善知识教训,致以身谤法!此光注重于敦伦尽分之来由也。又见多有收许多徒弟,皆不是真修行人。故发愿不收徒弟。见僧人向人化缘之卑鄙,故不愿做住持,做法会。今老矣,尚不至有负初心,而甘守讨饭本分,庶已生西方之友人,不在莲台中诮我也。————《复屈文六居士书二》
龙梓修、濮秋丞,十八年,拟以一千六、七百圆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为光说。光令以此钱打念佛七,彼便舍不得用,用几百圆念佛耳。使光赞成彼做水陆,则二人均须八百多圆。可见世间人多多是好闹热铺排,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与普度孤魂也。——《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
五台山广济茅篷(或称寺)。山上各寺及碧山寺子孙串通一气,并五台山区长、县长皆与彼串通一气,欲将广济茅篷僧逐下山,以便彼等吃肉喝酒,人不经见。以广济茅篷皆成年修持之人,两相形比,自己觉得太难为情,而又不肯改良,致成诬谤,谓茅篷之僧恶于本山僧十倍。区长、县长受贿,致阎锡山、赵戴文亦以为真,其势甚危。胡子笏在山,亦无法可设,遂与广慧和尚同来见光,将事实一一说明。光令茅篷大众念文殊菩萨,当有感应。初,台林逸来报国寺皈依,彼系山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光以此事托他与赵次陇(即赵戴文)详细说之。次陇前与光通过信,未曾晤面。林与赵说,赵遂派僧俗十人上山料理。与碧山寺子孙一万元,前已与过几次,约二、三万元,令彼迁出。(移去二十余里)才成了一个清净道场。——《复无边居士书一》
隋道绰禅师一生专弘净土,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可知一年之中当讲四、五遍,不以繁重为忌,唯期人各悉知。今人则必不肯如是,重重屡讲也。古人以利人为本,今人以求名为本。若专讲净土,人或见轻,所以不肯专精致力于一法也。——《复郭汉儒居士书二》
一后生,其人函祈皈依,过二、三年来函云,要遍通佛教各宗,遍通各国语言,要把佛法流布全球。光谓汝所说者,从古法身大士也做不到。汝是何时人,何不自量?若仍不改,后必魔死。过二、三年决欲出家,光抱定永不收徒之愿,明道师招来出家。人颇老实,绝无勇猛勤学之志。事非己分,任何等需要亦不肯代人之劳。——《复德诚居士书》
闻一商人某,其母死大殓时,大孝子与来客饮酒哗拳以为乐,其心已死。使稍有天良,决不如此,诚可谓实行兽化。然兔死狐悲,彼反不如异类矣。——《复张觉明女居士书八》
某某君者,忤逆不孝,居心险恶,貌虽学佛,心与佛悖。是人生若不遭横祸,死亦必定堕落。——《复蔡契诚居士书九》
福建黄慧峰,每以诗相寄,稍有薄信,光为寄各书,彼复求皈依,(与光年岁相等)后又要出家,光极陈在家修行之益。彼自诩为发菩提心,实则求清闲,为儿孙减养老费也。且其言决裂之极。光曰:“我在人家寺里住三十年,一身已觉多矣。况汝又来依我出家,汝决定要来,汝来我即下山。何以故?我自顾尚不暇,何能顾汝乎?”从此永不来信矣。——《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今之僧人,多系俗派,四十、五十,也举行祝寿,光一生闻见僧祝寿代为发羞。有以此事语光者,光曰:“我宁受斩头之刑,不愿闻祝寿之名。”有欲为光祝寿者,是拉光于最下劣之下流坯一派也。——《复夏寿祺居士书》
俗某某者,僧某某者,皆以堪作佛祖之姿,为自他塞人天之正路,掘地狱之深坑。其源皆由于乃父乃母初未尝以因果报应之若事若理,以启迪之故也。因果不讲,则名实绝不相应矣。而况欲得为圣为贤,成佛作祖之实效乎哉?因果二字,为今日救国救民之正本清源,决定要义。舍此则无术矣。——《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某某五、六年前,来往信札并发愿文,甚真切。光以彼僻处山间,兼且贫寒,寄去经书甚多。当地因彼劝导念佛者颇众。彼则近一、二年,直是下劣不堪,吃乌烟,犯邪淫。经光警戒,已经半年,尚不改悔,直是专待入地狱耳。——《复唯佛居士书》
民九年,常州庄蕴宽到普陀法雨寺,作一首诗,光往彼房与光。光视之,笑笑,放在他桌子上,不拿去。何以故?以帽子太高,万不敢戴故。然世之好名者,尚求人为己做高帽子。光与彼心相不同,彼以为荣,光以为辱。——《复袁常居士书三》
前朝有某大员,学问、功业、品行为世所钦。六十以后,遂放恣无度,某名誉一落万丈,诚可惜可怜也。学佛之人,古今亦有。初则知见甚高,极力自利利他。后则知见僻谬,且引一班人学己邪知谬见,为可悲可痛。究其受病之源,皆因好戴高帽子,致无知识之人各以高帽子为彼戴。戴之已久,正知正见已失,完全成邪知邪见。纵欲救援,反成按剑,只好任他去。凡好心学佛者,皆当令其立志自省,庶不至成此结果也。——《致杨慧通居士书》
民国十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十年正月出书,系二本之《文钞》。)即以照片小传请。光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决不肯随波逐浪效彼之所为耳。——《复李慧实居士书三》
光已七十有九,再过三十二日则八十矣。然朝不保夕,恐未必至八十而死。无论在生已死,切不可用今人之恶派妄为赞誉。光《文钞》中,于我父母师长均不提及者,盖恐人疑为饰说,致成大辱耳。今人父母师长去世,求名人题赞。光极不愿随顺此恶派,而辱及其亲与师也。我死之后,当极力提倡净土法门。令见闻者生为贤善,死生乐邦,此则唯功无过。若妄作赞诔,则是毁之于众也。——《复真净居士书》
数年前有游学生数十住法雨寺,夜亦做戏。教员一边坐视,彼便妆和尚,接香客,实侮僧。光闻之,不胜痛惜。堂堂学校,令生徒作此无益之事?——《复康寄遥居士书二》
昔普陀一老僧行路,适腿碰其凳,遂将凳踢倒,连踢几脚。此种知见,皆因任己我慢,绝不返省之所致也。——《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普陀法雨寺,光绪十几年,一饭头师,虽一、二百人之饭亦连汤干。此人当了数年,所省柴火日须一、二担,且多出饭,饭还养人。后一饭头,每顿须撇几桶汤,梢水桶满,则倒之阴沟。库房、客堂执事不过问。可知此饭头一年遭践常住柴火米汁,其罪大矣。——《复袁德常居士书四》
一幼僧佻僻非常,一切人皆莫如之何,其师因浼光教训。(其师与光系至交)光说其所以,以人当时面无血色,已惧之不已。后送来,光与彼和气详说,令勿违我命,违命则决不轻恕。彼心虽畏惧,究未亲试,不二日即犯规矩。光将打,与彼说其规矩:“不许动,不许哭。”未打先避。光曰:“此第一次,不加罚。再避,则定罚。”遂打,如植木然。从此半年,未须一高声说,此光绪十二年事。——《复卓智立居士书七》
顾君友人潘承锷君(二皆苏州人。顾为宁波黄道尹之西宾,皈依谛闲法师。)与顾甚厚。顾劝之念佛,彼致书反难,谓“不能生信,更为滋疑。”顾以其书寄光,令辟驳之。光将书寄去,谓“宜勿投”。顾即致书云:“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断兄之疑,因求某法师为书。其书已寄来,但其语言毫无谦逊,直言无隐,不避忌讳,恐致冲突,故不敢寄。”彼云:“我病深,非虎狼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飞寄。”顾即寄去,其心佩服,皈依谛闲法师。而畏光之直口,绝不一通音问。——《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
光一生不入社会,独行其志。在普陀时,初常住普请吃斋亦去。一顿斋,吃二、三点钟,觉甚讨厌,遂不去吃斋二十多年。——《复屈文六居士书一》
某法师往生记,当按实事另作。切不可无中生有,以启无知之人效尤。则似是弘法,实开败法之衅,其祸大矣。——《复觉僧居士书》
湖南人吃饭,不吃尽,此风甚劣。食为民天,何敢暴殄?虽一粒半粒,亦不宜弃。人若抛撒五谷,必定来生无饭吃,今生亦有即得饥饿之报者。人若蹧践字纸,必定来生无目及愚痴无知。——《复马宗道居士书一》
某某之为人。盖宿有因缘,而因循不振者。彼系金坛冯梦华弟子,与魏梅荪为同门。前数年曾见过光,去岁以某事颇感光,遂与梅荪说,欲皈依。曾托梅荪求光,为雷峰塔经题数句作纪念。然以因循,故未即行。至云亲族骇怪,乃借此以饰懒惰懈怠,不肯修持之迹耳。夫学佛法者,曷尝弃舍本宗,但于本宗外,加以佛教之修持耳。世之人作种种恶事,不惧亲族之骇怪,今也学如来之大法,反惧亲族之骇怪,是尚得谓之为真心学道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吾行吾志,谁能御我,令不为圣贤之徒?况学出世之大道乎?——《复马宗道居士书二》
某某近几年颇受新潮之影响,今夏大病,始知惭愧,云欲十年用功,方始宏法也。现今之世,除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纵佛、菩萨、圣贤同出于世,亦末如之何!——《复林赞华居士书四》
民十五年,四川陈敦五夫妇来普陀皈依,谓光曰:“我最好阳明,阳明完全是佛学,何以又或有辟佛处?”光曰:“汝知彼之心否?”曰:“不知”。光曰:“彼为入文庙耳。”遂大声叫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程、朱以后之理学,皆偷学佛,皆极辟佛,实皆为入文庙耳,不计圣道之利害也。——《复常逢春居士书一》
王高氏娴熟经典,而作不敢妄想生西之说,其心志之卑劣,亦何至于此极?其平日所亲之师,亦系盲修瞎炼之辈。使其师知净土法门,何得长作此想。若不求生西方,决定不许皈依。肯求生西方,则可许皈依。净土法门,以真信切愿念佛,决定求生西方为宗旨。若念佛人不愿求生西方,即为违背佛教。譬如王子寄居他国,不信自是王子,但愿终日乞食,不至饿死,便为志得意满。其知见之下劣,能不令人怜悯乎?——《复杨宗慎居士书》

无得居士既有六十老父,何得要出家?使不出家,无由闻法修行,尚有可原。今藩篱大撤,在家人研究修习者其多如林,得利益生西方亦常有其事,何得要离亲出家乎?此事光绝不赞成。按实说,当今修行,还是在家人好,何以故?以一切无碍故。出家人之障碍比在家人多,是以非真实发道心者,皆成下流坯,无益于法,有玷于佛也。——《复唐大圆居士书》
普陀蚌壳有佛,乃奸人伪造,店中长年出卖,已数十年矣。乃剖其壳作两半,安铜佛像于内,而复合之。有云系取活蚌,剖壳安之,仍养于水中,待长浑全,则取而卖之。其死活造法,究不清楚。伪为,乃的确之极。噫!奸人求利之心,亦可谓委曲周到之极矣。而一张人皮,往往由兹卖却。可不哀哉?——《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
昨日灵岩当家妙真师来,合寺大众减省衣单之费,共凑二百二十八圆。今日已令自送曹府,用赈江北。前次汉口发水后,灵岩凑一百二十八元,送上海交汉口赈灾会。此诸师之施,可谓竭尽无余之施。——《复袁孝谷、曹崧乔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今年六月,汉口初发水灾,明道师往上海代捐一百圆。后其水更大,又捐一百圆。一弟子以芜湖水灾,函祈募赈。光复彼信,谓光一向不募捐,况在关中。后一弟子曹崧乔往江北赈灾,打电令光劝捐,光送印书洋一千赈灾。高鹤年来函祈救灾,光令交二百三十元。此今年赈灾所出者。光作此说,非自夸功,盖欲汝等同皆发心,随分随力而为救济。有力出力,无力出言劝有力者,亦是善事。
又今之女人首饰、臂钏、耳坠、戒指均不可带,带之则招祸。若留之与儿女,则是贻祸于儿女。若死后附葬,必致掘坟露尸,其为辱也大矣。若肯赈灾,则是送祸去而迎福来矣。若女界中肯如此以施,则其款巨矣。彼高邮、邵伯之富人,在先何尝不念念为子孙谋,不肯少行救济。而大水一来,房屋、器具、人口通皆七零八散,十不存一。每村数十家,求一锅一灶而不可得。曹崧乔在扬州买锅、灶、米、火柴,数十家给一锅,以大船装去。村间用小船往放。说之令人堕泪。有房未倒者,蛇与蜈蚣均盘踞其上,人欲上房亦不敢上,树上亦然,可怜可怜。彼女人尚将招祸之物不肯用以救济,则后生他世恐亦罹此灾,而无人肯救也。——《复刘汉云、杨慧昌居士书》
吾乡一居士无子,多方祈祷均不应,遂娶一妾,而妻妾不和,颇生闲气,又不生。一友为计画,拟于远乡娶一妾,不来家中,每年其友来往一、二次,以期生子。有以此事告光者,光闻之,不胜慨叹。以一少年女子独居于数百里之外,此女不生外事即是大贤,恐百千人中,也难有几个。况此一女乃自成一家,尚须用人,其费用颇可观。幸而生子,好讥议者必有暗昧之污蔑。不幸而又不生,则此女一生孤寂,其夫一生供给,真成自投牢狱,为女作奴,可不哀哉?——《复胡奉尘居士书》
秦吉了,劝彼念佛,云“不会”,云“什么”?见念佛,则狂笑,此乃毁谤佛法之恶习。及日常教之,则肯念,果有常念佛人,彼随之日日常念,安知不如宋之念佛八哥,念佛立化,埋而莲花生于墓上,掘土视之,其根在于舌端乎?人固如是,物亦如是。——《复张觉明居士书二》附:张觉明居士来书:“有一只秦吉了,何君所养者,能说能笑。教其念佛,先时十分憎厌,非说“不会”即说“什么”?见弟子拜佛,则狂笑不已。复耐性,每日教以四字真言,今已肯多念耳。
四、五十年前,天津大悲院完全围于兵营中。狐仙作崇,营官不能住,请大悲院老和尚来,则平静无事。营官很尊重,大悲院扫院地各事皆营兵日日为之。夜间外面放焰口回,喊营门即开。又有搭船夜间来挂搭,亦无所禁。木渎有兵一千,均住于民家。闻近来之兵尚驯良,不横暴。当此之时,一则以修持求三宝加被,一则以修持令主兵敬信。苏州西门外灵岩寺下院亦住兵四、五十,尚善良,不在院内烧荤菜,此亦很难得之事。——《复念佛居士书》
自民十七,南洋商家多半破产。有往南洋募缘者均不敷川资。南洋以橡皮胶为第一出产,英政府把持不许贱卖,每担卖一百六十多元。十七年受某国人骗,谓若不贱卖,再过两年,吾国树大,则无人买汝之货矣。遂偷卖。一家而全市卖,不到一月,大商家倒数十家,现在更贱得不堪。光一弟子将此情景说与光。故云南云栖寺虚云和尚之徙修圆以云栖寺亏空,欲往南洋化缘,光劝勿去,不听,后由云南汇款去,方得回国。南洋所化,尚不足供川资耳。——《复周伯遒居士书廿三》
今午一句余钟,江梵众居士持书至。问其为何而来,言欲观名胜,并参拜高人。现在时局,危险万分。光令速即回川,彼云:“可迟一星期否?”光云:“汝无要事,何得故迟,设若战事一起,则进退维谷矣。明日即归,以免高堂依门之望。”彼云:“明日定归。”随即告退。——《复谢慧霖居士书八》
光绪十八年,光在北京阜城门外圆广寺住。一日,与一僧在西直门外向圆广寺走。一十五、六岁乞儿,不见有饥饿相,跟着要钱。光云:“念一句佛,与汝一钱。”不念。光云:“念十句佛,与汝十钱。”还不念。光将钱袋取出来令看,约有四百多钱,为彼说:“汝念一句与汝一钱,尽管念,我尽此一袋钱给完为止。”还不念。遂哭起来,因丢一文钱而去。此乞儿太无善根,为骗钱,也不肯念。——《复张觉明女居士书八》
曹崧乔多年来专办周济地方贫民之义举,又筹陕赈十余万圆。昔其父曾任豫藩,遗爱在民,今崧乔又广其遗爱于陕,更不辞劳瘁,为江北百万生灵,筹安全之策,可谓能世其德,有加无已者矣。袁孝谷,丹徒人,其尊翁亦名太史。本人宦苏多年,奉公守法,于地方人民,感情甚深。而且侨寓苏垣,赋闲净修。秋间江北水灾,振古未有。江苏水灾义赈会,于八月二十八日急电曹袁前往办赈,刻不容缓。随即起行至扬,先会官绅,次设赈局,然后分头调查各自灾状。随即函电向苏州,及各方慈善家呼吁,为灾民请命,陆续得洋十五万左右,其单夹棉衣鞋袜等,或新或旧,共有十余万件,棉被千余条,锅巴药品,为数甚多。别处之款,得十程之四。大数之款,及诸衣物,均系苏州所捐。一以曹袁二人,向为地方人士所敬信;一以苏州为维卫、迦叶二佛所住之地,而唐宋之陆元方、范文正之流风善政犹存,故其人民,多皆慈善仁爱,视人犹己,得有此大批之赈款也。——《〈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赈经历报告书〉序》
明,紫柏大师,一生兴十余处大丛林,不作方丈,不收徒弟,工成即去,置诸度外。妙峰大师,凡寺塔桥梁道路之工程,他人不能办者,请彼办,经手即成,成即告退。当修造时,或令其徒代理,工成,绝不安己一人。其心之正大光明,数百年后闻之,令人钦佩不已。——《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昔阿耆达王,一生奉佛,坚持五戒。临终因侍人持拂驱蝇,久之昏倦,致拂堕其面,心生瞋恨,随即命终。因此一念,遂受蟒身。以宿福力,尚知其因。乃求沙门,为说归戒。即脱蟒身,生于天上。是知瞋习,其害最大。古有极毒之人,现身变蛇。极暴之人,现身变虎。当其业力猛厉,尚能变其形体。况死后生前,识随业牵之转变乎?《华严经》云:“一念瞋心起,百万障门开。”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学菩提道,忍辱护瞋心。”如来令多瞋众生作慈悲观者,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既是过去父母,则当念宿世生育恩德,愧莫能酬,岂以小不如意,便怀愤怒乎?既是未来诸佛,当必广度众生,倘我生死不了,尚望彼来度脱。岂但小不如意,便生瞋恚,即丧身失命,亦只生欢喜,不生瞋恨。所以菩萨舍头目髓脑时,皆于求者,作善知识想,作恩人想,作成就我无上菩提道想。——《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
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绝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年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光未从师,始终由兄教之。)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先师意光总有蓄积,云出家则可,衣服须自备,只与光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此地苦寒,烧饭种种皆亲任。)后未三月,吾兄来找,必欲令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则可。光知其是骗,然义不容不归。一路所说,通是假话,吾母倒也无可无不可。次日兄谓光曰:“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光只好骗他,遂在家住八十余日,不得机会。一日吾大兄往探亲,吾二哥在场中晒谷,须看守,恐遭鸡践,知机会到了。学堂占一《观音课》云:“高明居禄位,笼鸟得逃生。”遂偷其僧衫,(先是吾兄欲改其衫,光谓此万不可改,彼若派人来,以原物还他,则无事,否则恐要涉讼,则受累不小,故得存之。)并二百元钱而去。至吾师处,犹恐吾兄再来,不敢住,一宿即去。吾师只送一圆洋钱,时陕西人尚未见过,钱店不要,首饰店作银子换八百文,此光得之于师者。
至湖北莲花寺,讨一最苦之行单(打煤炭、烧四十多人之开水,日夜不断,水须自挑,煤渣亦须自挑出,以尚未受戒,能令住,已算慈悲了)。次年四月副寺回去,库头有病,和尚见光诚实,令照应库房。银钱帐算,和尚自了。光初出家,见“杨枝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之对,并《沙弥律》,言盗用常住财物之报,心甚凛凛。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气味者,均不敢用口舌舔食,但以纸揩而已。杨枝灯盏者,杨歧方会禅师,在石霜圆会下作监院,夜间看经,自己另买油不将常住油私用。宝寿生姜者,洞山禅师(宝寿乃其别号),在五祖师戒禅师会下作监院,五祖戒有寒病,当用生姜红糖熬膏,以备常服。侍者往库房求此二物,监院曰:“常住公物,何可私用?拿钱来买。”戒禅师即令持钱去买,且深契其人。后洞山住持缺人,有求戒禅师举所知者,戒云:“买生姜汉可以。”《禅林宝训》卷中,五十四、五两页,有雪峰东山慧空禅师答余才茂进京会试、求脚夫力书。大意谓:我虽为住持,仍是一个穷禅和。此脚夫为出于常住,为出于空?出于常住,即为偷盗常住。出于空则空一无所有。况阁下进京求功名,不宜于三宝中求,以致彼此获罪。即他寺有取者,立应谢而莫取,方为前程之福耳。
近世俗僧多多以钱财用之于结交徒众俗家,光一生不愿结交,不收徒弟,不住寺庙。自光绪十九年到普陀,作一吃饭之闲僧。(三十余年,未任一职,只随众吃一饭。)印光二字,绝不书之于为人代劳之纸,故二十余年很安乐。后因高鹤年绐去数篇零稿,登《佛学丛报》,尚不用印光之名。至民三、五年后,被徐蔚如、周孟由打听着,遂私为征搜,于京排印《文钞》(民国七年)。从此日见函札,直是专为人忙矣。遂至有谬听人言求皈依者,亦不过随从彼之信心而已。富者光亦不求彼出功德,贫者光又何能大为周济乎?光绪十二年进京,吾师亦无一文见赐。后以道业无进,故不敢奉书。至十七年圆寂,而诸师兄弟各行其志。故四十年来,于所出家之同门无一字之信,与一文钱之物见寄。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乡,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以民国来陕灾最重,若与彼信,彼若来南,则将何以处?无地可安顿,令彼回去,须数十元,彼之来去,了无所益,岂非反害于彼?故前年为郃阳赈灾,只汇交县,不敢言及吾乡。(吾村距县四十多里。)若言及,则害死许多人矣。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近二、三年专办陕振)来申,与三、四居士凑一千元,祈子桥特派往振吾本村。西村亦不在内,然数百家,千元亦无甚大益。由此即有欲来南者,一商人系吾宗外甥,与光函云,有某某欲来南相访者,作何回答?光谓汝若能照应,令其得好事,则甚好。否则极陈来去之苦,并无益有损之害,庶不致于害死彼等也。此事真师一番好意,并未细想所以,兼又不与光说。及光知,事已成矣,无可挽回。无论何事,先须防其流弊。光岂无心于吾家吾村乎?以力不能及,故以不开端为有益无损也。——《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今夏有友自哈尔滨来,言其地烟禁大弛,亦有二、三友人欲戒而苦无良方。光先闻陈锡周“戒烟方”灵得非常,为从来所未有。候其来山,令开出寄去。又开一张与本寺副寺,令其送人。以彼曾在商务中做过事,交游必宽,企其普遍流传。至十一月间,哈尔滨有信来,言光所寄方,灵得非常,代为戒好友人致谢,不胜欢喜。因问本寺副寺,彼言其友汪蟾清,其内人以气痛吃烟,后欲戒之,即买市卖药丸服之,终不断根,若不吃药,烟气二病即发。得此方一料服完,烟气二病,化为乌有。其子开汪李济堂药店,生大感激,印其方送人,并依方制成丸药,药水,以期济人,于自己各店卖之。光即令要二百张方子来,凡远近知交有信来,皆为附寄一张,有力者令其排印广传。宜将此方长年上报,俾举世咸知,则功德无量矣。——《与徐蔚如居士书四》
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窠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恁么道?”窠曰:“三岁孩童虽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须知此语乃一切学佛人之总关切要语。——《复马契西居士书一》
秦地之民,素称良善。世风日变,法律废弛,游手游食之败类遂得肆意横行。勾通当地坏人,劫掠乡村,惨不忍闻。近数年中,有自秦来言及秦地现状,无不哽噎涕零。盖土匪一至,遇稍有余裕者,则炮烙烧燎,无所不施,以期其尽献贮积而后已。其苦不堪,势必尽献。而一受此刑,即当时不死,亦难久生。多有富人之室,通皆掘地三尺。凡灶炕墙壁,悉皆毁坏,以求埋金。其淫掠之迹,为千古所未闻。以官府不能制,百姓无控诉。直同长处地狱,了无出期矣。此大帮土匪也。至于小帮,其人众虽少,其酷烈亦然。其来多在夜间,凡闻有此消息,天将暮,先送女人于村外,或田禾中,树林间,坟墓间。即风雨霜雪,亦不敢归,小儿啼哭,则以物杜口,每有闭气致死者。男子多宿于房上。土匪一过,如火燎原,了无生物。此种苦况,说不能尽,尚不知其何所底止。以是之故,凡稍有家资,可逃出外方者,悉皆弃祖籍,而逃命于他乡矣。上海逃者,不计其数,况各处乎?止一土匪,已属不堪,再加以靖国一军,数年交战,其兵所到处,蹂躏淫掠,何可名言?呜呼!秦人何辜,罹此鞠凶?——《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方峻生可谓难舍能舍矣。虽然,尚须为彼后日过活虑。如其所有田地可以养家,则彼已发心送法云寺则便作彼之功德。如其所有不足为养,当将此田作为法云租田,岁出租若干,任凭法云寺种竹木五谷蔬菜,以作慈幼院工农场之备。如此方可彼此各尽其道,彼此各得其益。若彼舍此田,则用度无出,吾人心中实有不适悦豫乐之大者在也。——《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
南京打七,吃点心度数过多,不但不能心归一致,且令食不易消。当以多食为戒,两粥两饭斯可矣。——《复罗鉴端居士书二》
香烟之毒,甚为酷烈。于众会时当为提倡,劝勿吸食此物。吸久人必短寿。妇女吸多,便断生产。此吾一弟子亲见外国女教员说与女学生者。——《复周伯遒居士书四》
杭州市政府令人捕街上野狗,杀而丢之钱塘江中,已摔死百数十条。佛教会祈彼送之佛教会,已有近二千只。每日一狗须一分五厘食费,二千则日需三十元。尚有派人料理,死则焚烧等费。光亦捐一百元,又拔友人助款四、五百元。此时所最急须之款,即养狗费。——《复周伯遒居士书十一》
光回陕事,实为不易。以陕地撩乱,又兼寒冷,若将衣物通丢了,到秦则置不起。若带上,则东西累堆,实属两难。以故光绝无回秦之心。况现在普陀修山志,虽非光自主,然光固不能置之度外。——《复康寄遥居士书三》
印光生即病目,今则惜人之目甚于己目。每见聪敏少年多皆近视,问之,则曰看小书所致。窃谓书肆书贾,唯以稀奇炫异为求巨利,不问与人有利有害,瞒心昧理力求获利之道。——《复丁福保居士书三》
近来佛学昌明,政府特请通法高僧,常至监狱,开示佛法要义,并生死轮回之因,与了生脱死之法。俾彼各知心是佛心,自当遵行佛行。欲了生脱死,非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决难如愿。彼等一闻,如临明镜,妍丑自知。如遇慈母,庆幸莫喻。经声佛号,无间晨昏,即监狱为道场,即囚犯为法侣,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一入其中,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彼谓佛学无益于国,有害于世者,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以自误误人也。而本监狱官,因发大心,特请具德法师,于甲子元旦,普与监狱诸佛子,说三归五戒。冀其以归戒制服身心,以致妄想执著,复归乌有。而智慧德相,彻体圆彰矣。——《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三归五戒序》
数十年前,湖南一大封翁做寿,预宣每人给钱四百。时在冬闲之际,乡人有数十里来领此钱者。彼管理者不善设法,人聚几万,慢慢一个一个散。其在后者,以饿极拚命向前挤,因挤而死者二百余人。尚有受伤者,不知凡几。府县亲自镇压不许动,死者每人给二十四元,棺材一只,领尸而去。老封翁见大家通惊惶错愕,问知即叹一口气而死。不几日其子京官死于京中。是以无论何事,先须防其流弊。——《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宋慈云忏主赴苏讲经,听者日万夜千,屠沽为之不售。法道之盛,诚所未有。慈云惧之,恐致意外之虞,遂即中辍。夫慈云乃具大智慧,大辩才,兼有神通之高僧。当国家成平,人心淳善之时,尚如此慎重。夫一法既立,百弊潜生。不谨于始,决难令终。——《复王与楫居士书》
宋吕文穆,读书土窑,乞食活命。一僧怜而供给之,遂得高中魁选,致君泽民。故发愿有云:“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不信三宝者,勿生吾家。”盖其所感深也。唐一行,明妙峰,皆孤儿也。由得为僧,遂致道传天下,德被兆民。是知神龙之雏,每有沙碛之困。仁人能以斗升这水济之,待其羽翼既成,风云际会,便能普天之下,悉降甘霖。——《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
无锡一当兵的坏人,曾在袁总统下当亲兵,遂习成坏性。吃喝赌冶游全来,烟瘾甚大。将及饿饭,眼已看不见,年已五十七、八。其兄死,秦效鲁去吊,见其苦况,极力劝诫,其烟酒肉即日尽断。日常念佛,眼遂好。居然成一善人,提倡念佛,乡人不敢与往还。后疟疾大发,彼一一为治,通好,从此乡人皆相依从。四月间曾带十余人来皈依,居然一老修行居士。若此人者,可谓勇于改恶迁善矣。——《复张觉明女居士书八》

佛在世时,一老人欲投佛出家,五百圣众观其八万劫来毫无善根,拒而不纳。其人在祇园外号哭,佛令召来与之说法,即证道果。五百圣众莫名其妙。问佛。佛言:此人于无量劫前,因虎逼上树,念一句南无佛,遇我得道。非汝等声闻道眼所能见也。是知肯念佛固好,不肯念佛,为彼说,彼听得佛号,亦种善根。虽戏顽而念一句,亦于后世定有因此善根而发起修持者。故古人大建塔庙,欲一切人见之而种善根。——《复张觉明女居士书九》
有同乡芹浦刘在霄先生者,清介之士也。世德相承,笃信佛法。今夏来山见访,谈及近来中外情景,戚然曰:“有何妙法,能为救护?”余曰:“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须令断因。因断则果无从生矣。故《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遂将《安士全书》示之,企其刊板广传,普令见闻,同登觉岸。先生不胜欢喜,即令其甥赵步云出资七百元,祈余代任刊事。——《重刻安士全书》序二
民国十年,光至南京,魏梅孙(系翰林,时年六十。)谓光曰:“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师之《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光谓:“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祈熟读光《文钞》中《南浔放生池疏》,当数数读,自不能吃肉矣。”此系八月十二日话,至十月,彼六十生辰,恐人情有碍,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即长素矣。——《复卓人居士书》
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书,深信念佛法门。弱冠入泮,遂厌仕进。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骘文广义》,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同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福报,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
宋之丞相张商英,商英初不知佛法,因游一寺,见佛经庄严殊胜。忿然曰:“胡人之书,乃如此庄严,吾圣人之书,尚不能及。”夜间执笔呻吟,莫措一词。夫人向氏,颇信佛,因问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无佛论耳。”夫人曰:“既然无佛,又何可论,且汝曾读佛经否?”曰:“吾何肯读彼之经?”曰:“既未读彼之经,将据何义为论?”遂止。后于同僚处,见案头有《维摩诘经》,偶一翻阅,觉其词理超妙,因请归卒读。未及半,而大生悔悟,发愿尽此报身,弘扬法化。于教于宗,皆有心得。所著《护法论》,极力赞扬,附入大藏。徵宗朝入相,时旱久,夜即大沛甘霖,徵宗书“商霖”二大字以赐。盖取《商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甘”之义以褒之。——《重修〈九华山志〉序》
虚度七十,来日无几。如囚赴市,步步近死。谢绝一切,专修净土。倘鉴愚诚,是真莲友。——《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
芜湖有一女回回,深信佛法,前年函祈归依,彼常劝人念佛。有一极聪明之儒,不信因果,不信佛法。彼与其人辩论,令看《文钞》,不数篇而祈彼代祈皈依。此盖以严正服人,故人敬奉其言。——《复宗净居士书》
提倡因果报应,莫善于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彭定求从小日诵此二书,至中状元作尚书时犹日日诵之。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非谓读此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之要矣。——《复朱仲华居士书一》
切实修持,将身作则,认真提倡。至诚感人,人自乐从。莒县监狱官李丙南提倡不二、三年,莒县人皈依者已有一百多,皆士农工商政界之男子。——《复宋慧湛居士书》
关絅之之相信佛法,乃因《安士全书》木刻本起。志圆为之讲说,从之生正信心。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由于《龙舒净土》文下卷,足知书之益人也,深且远矣。——《复李觐丹居士书三》
沪战时,苏州曹沧洲居士之孙,奉父命由沪赴苏,迎其三叔祖及叔父等往沪,彼叔祖叔父通不愿去。其人以其妻之珠宝等缠之于腰,坐小火轮往沪。忽强盗来,欲跳上岸,堕水中,所带金珠,可值二三万,均送于为己换衣之一人,而自称贫士,为教蒙学之教师。倘大强盗知,则又不知要几多万令赎,岂非钱财之祸人耶?今人只贪目前便宜,不能看破,为钱财而吃亏,其例甚多,不胜枚举。——《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玉嵀大师,乃光五十年前之同学。其性情质直而谦和,其修持切实而诚恪。不为住持,不收徒众,与光相埒。注重持律与念佛,故晚年多刻律宗之著作。盖欲坚其基址,冀来哲同生极乐。幸师已归安养,愧光犹在此世受惊噩。愿师祈佛垂接引,庶可同随如来学。——题玉嵀大师心迹颂》
光无状,自光绪七年离家,至今已五十年,依然故我。业障未消,道业未成,无面目以回本乡。虽前承陈柏生、刘雪亚二督帅,函劝回秦,但自愧实甚,不肯应命。以致先祖坟墓,并父母坟墓,均未一往礼拜,不孝之罪,直无可忏,每一思之,汗为浃背。居士秉救济之婆心,行平等之法行,不以寒舍为辱,而一为观察,可谓屋乌推诚矣。又复往视光之祖茔,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光阅至此,不禁潸然惨凄者久之。然而光之为人,绝不愿留虚名以污人耳目,但期临终仗佛力以往生,则所愿足矣。——《复杨树枝居士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