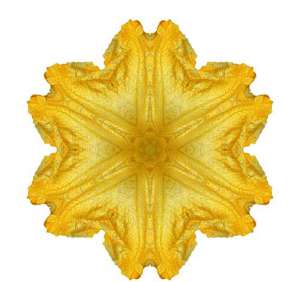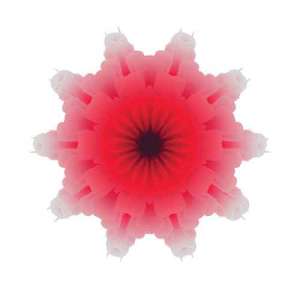印度的近代佛教
发布时间:2019-11-14 10:01:18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经过回教歼灭之后的印度佛教,在我国南宋宁宗(西元一一九五-一二二四年)之时,即告消声匿迹。在政治方面,回教人入侵之后,建立了莫兀儿帝国。相继而来的是欧洲的白人,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最后便由英国全面统治,而於西元一八七七年成立了英印帝国,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兼做了印度的皇帝。
迄西元一九四八年,始获得独立。但在独立以前的一年,已经由於回教徒及印度教徒的相互仇视而在英国政府的监督下,将印度的版图,分割为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了两个国家。
正由於异民族的长期统治,同时有若干知识分子也受了时代思潮的激动,所以争取民族独立,主张民权平等的要求,便日益迫切。为了团结全民以对抗外侮,为了同情贱民阶级的悲苦生活,就有甘地先生应运而起。甘地坚持不合作及不用暴力的主义,以反抗英国政府;他穿上了贱民的服装,以提高贱民阶级的自尊。
我们知道,印度教是阶级主义的宗教,印度教之能在回教入侵数百年后尚未灭亡,是由於他们的战斗精神,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贱民平等思想,并非印度教的产物,倒与佛教吻合。甘地自己也说:“印度教中把不可接触列为教规,那是一种腐化的部分,或只是一个赘瘤。”又说:“请看菩萨(系指释尊)的慈悲,不但施於人类,而是广泛及於一切生物。”(《甘地自叙传》第七章)
事实上,今日的印度人民,已不仇视佛教,且以佛教发源於他们的国家为光荣,甚至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说:“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星云法师《海天游 [跳-兆+宗]》一六六页,一九六四年初版,《觉世》旬刊社出版)
因此,佛教在印度,已经露现了复兴的曙光,虽其人数的比例,尚是印度各大宗教中的第六位,它们的次第如下:
(一)印度教:三亿零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六人。
(二)回教:三千五百四十万零一百一十七人。
(三)基督教:八百一十五万七千七百六十五人。
(四)锡克教:六百二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四人。
(五)耆那教:一百六十一万八千四百零六人。
(六)佛教:一十八万零七百六十九人。
(七)拜火教(教):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人。
(八)犹太教: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一人。
(九)各部落原始宗教: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人。
以上统计,系出於一九六○年日本出版的《佛教大年鉴》一七页。其中所列 的锡克教(Sikhism),它由生於西元一四六九年的难能教主(Guru Nanak)所创,他出生於旁遮普地方的武士阶级,鉴於印回两教的冲突而研究各宗教教理,发现印回二教的上帝只有一个,它是超乎世间,而永恒存在。他主张内心的真纯信仰,不同意偶像的崇拜。
重视佛教
近世以来的印度,除了其民族独立运动需要佛教的思想,在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也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希望,由於印度佛教遗迹的继续发掘出土,以及梵文和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考察,已向世界公布:佛教虽是古老,佛陀的教义,却被发现仍是如此新鲜而合乎时代思潮的要求。
印度政府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特别设有考古部,派员四处探寻佛教的遗迹,如今,凡是已被发掘出土的,均加保护,并整理其环境,同时在加尔各答及鹿野苑(Sarnath)等处,成立博物馆,储藏陈列各项佛教的古物,以供来自各国的学者及朝圣者的观摩参礼。
据朱斐居士说:“印度政府在近十年来……将每一处通达圣地的公路上铺了柏油,各处圣地也装了电灯,并且在每一圣地,都建有政府的招待所,以接待各国来印朝圣的佛教信徒。政府机关首长的办公厅里,除了甘地先生的遗像外,多加上了一幅佛陀圣像。”(朱斐《空中行脚》三六页)
印度重视佛教的表现,尚有在一九五六年,由政府主办了释尊灭度二千五百年纪念大典。一九六○年,又在德里建设一所佛陀纪念公园(BuddhajayantiPark)。一九六四年,又由政府协助,在鹿野苑召开了第七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正由於政府重视佛教,凡是去巡礼佛陀圣迹的外国人,无不受到印度朝野的竭诚欢迎。例如西元一九四○年一月,太虚大师访问印度,即有这样记事的诗句:“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又於一九六三年,白圣法师率团前往朝圣,也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亲切接见。
但是,要介绍近代的印度佛教,必须记得另外两位伟大的居士,那就是达摩波罗及安培克两位功臣了。
达摩波罗
达摩波罗居士(Dharmapa-la Anagarika 西元一八六四-一九三三年),生於锡兰可伦坡的一家家具制造商的家里,他的家人信佛,却把他送往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受教育,但他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后来,他受到美籍的佛教徒邬克德上校(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 西元一八三二-一九○七年)的感化,便对佛教的信念坚固起来,进而研究佛教,接着便宣誓将以复兴佛教为其毕生的目的。
西元一八九一年,达摩波罗首先到印度巡礼了鹿野苑,见到昔日的圣地,竟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他又到了佛成道处的佛陀伽耶。当年他才二十九岁,正好是释尊出家的年龄。这次造访,给了他更多的启发,於是下定决心,就在那年十月的下旬,召开了重兴圣地的国际佛教徒会议。
西元一八九二年,他即以“印度教与佛教之关系”为题,初次在加尔各答传道,并创设大菩提会事务所,创《摩诃菩提杂志》,藉以联络各国教友。因此,他又访问了美国、夏威夷、欧洲、日本等国家地区,在各国教友的援助下,他的大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终於成立。他以佛教已被放逐了八百年之后,现又重回故乡而自慰,并且以此勉人。他说他要以佛陀超越一切阶级的信条,来奉赠给印度的人民。
达摩波罗居士在印度为复兴佛教,工作了四十多年,广传教义,培植人才,设立分支机构,便利朝圣的教友。例如在鹿野苑的摩诃菩提社,对於前往朝圣的人,均予借住,唯膳食自理;现在加尔各答的该社,也有专供朝圣教友们住宿的房舍。
他病逝於西元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但他给予印度佛教的生机再现之功德,将永为后世敬仰和赞扬。
安培克博士
安培克博士(Dr. Ambekar)本生於被印度教视为“不可接触”(Caste)的贱民之家,故他在少年时代即遭受到各种场合的歧视和虐待,印度教的种种制度使他深深地感到不满。后来有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认为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便协助他留学英国,并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二次大战后,印度独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长,又成为印度新宪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导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会制度的弊端,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实现佛教的四姓平等的社会,方能解救贱民阶级的疾苦。於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劝导他的贱民群众信佛,并於一九五五年发起佛教主义运动。
终於,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妇,率领了他的群众约五万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尔 (Nagpur)一个四十英亩大的广场上,由印度当代最负盛名的司塔维拉法师(Ven. U. Chandramani Maha-stha-vira),主持典礼,代表僧团,接受他们的集体皈依。同时皈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长尼奥基博士(Dr. M. B. Niyogi),以及梅令达大学院校长契拿司(Sri. M. B.Chitnavig)等社会名流。
可惜,这位虔信佛教的法学博士,竟於同年的十二月间,抱病出席於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四届大会时,在他演说之后,即与世长辞了。
但是,他对佛教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之后,所完成的一部《释迦和他的宗教》, 已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全印度佛教会议”中通过,被采用为印度新佛教徒的圣典。可见他对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影响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学者的活动
佛教在印度,自从印度教复兴之后,已为印度教所吸收,他们不以佛教为一独立的宗派,而是将佛教与湿婆崇拜及毘纽笯崇拜,视为同一个宗教。唯在锡兰方面,仍以巴利语圣典的传持,维系着上座部佛教的纯一的信仰。
近世以来,印度与锡兰两地,对於佛教虽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许多贡献。唯在印度的佛教学者,因其不能将佛教置於独立的地位,总以印度教作为正统的思想,所以不无缺点。然而,印度学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学方法,故能持一客观和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佛教。他们研究的对象,初受锡兰的影响,着眼於巴利语圣典;后来扩大范围,乃以梵文及巴利文圣典为主,做语言学及文献学的考察,旁及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设了专攻佛教学的大学和研究所,同时派遣留学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当然,印度佛教的复活,既是仰助於达摩波罗的反哺,在学术上的启蒙,也不例外,达摩波罗的摩诃菩提协会创立之后,即有几位印度学者,去锡兰研究巴利语,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学的研究基础。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佛教圣典协会(Buddhist Text Society)。在此之前,则有弥多罗(Ra-jendra La-laMirowa 西元一八二四-一八 九二年)、斯脱利(Hara Prasa-da sa-srowi 西元一八五三-一九三一年)和达斯(Sarat Chandra Das 西元?---一九一七年)三人,为近世印度佛教学的草创者。弥多罗著有《尼泊尔佛教目录》(Sanskrit BuddhistLiterature of Nepal 西元一八八二年),西 元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颂般若》的校订版。斯脱利曾协助弥多罗对於尼泊尔佛 教文献的整理,后来则亲自到尼泊尔做了两次寻访佛典的写本,并且校订了《不二金刚集》(Advayavajra-samgraha G. O. S. 西元一九二七年)。达斯乃为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驱,他进入西藏,踏访藏文佛典,并对喇嘛教进行调查的结果,除了撰写报告 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西元一八九三年)等之外,又於西元一九○八年校订了西藏语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树》,西元一九○二年则著成《藏英辞典》。
以上三人,也可算是“佛教圣典协会”的先驱者。此后,该会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报、校订原典、翻译和出版,与孟加拉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西元一七八四年)合作,成为印度学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达斯的弟子韦提耶勃莎那(Satis Chandra Vidya-bhu-s.an.a 西元?”一 九二○年),他曾协助达斯,担任佛教圣典协会的事务。他初学於加尔各答大学,后至锡兰研究巴利语佛教,归国后便任加尔各答大学的校长,他的专长是印度论理学,著有《印度论理学史》(History of IndianLogic 西元一九二二年)等,乃为研究因明学的基础书。他的继承者是白罗亚(Beni Madhab Barua
西元?-一九四八年),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历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学史》(History ofPre-Buddhist Indian Philosophy 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论书。
同在加尔各答大学内的印度佛教学者,尚有巴他茶利耶(Vidhushekara Bhattacharya)与B.C。劳(Bimal Churn Law)两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献为主,后者则为巴利文文献的大师。
巴他茶利耶曾於西元一九三一年,将龙树的《大乘二十论》及提婆的《四百论》由藏文还原为梵文,西元一九二七年则将《因明入正理论》译为印度文,并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ionof Buddhism 西元一九三二年),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订《瑜伽师地论》的梵本中。
B. C。劳的学术领域很广,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对於佛教史、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达五十册,乃为近世印度学者之中着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罗亚的后继者,他的主要着述有巴利语圣典的校订、英译,和传记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献史》(History of PaliLiterature 西元一九三三年)、《古代印度之种族》(rowibes in Ancient India 西元一九四三年)等。

同为白罗亚的弟子,尚有达脱教授(Narinaksha Dutt),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诸相及与小乘的关系》(Aspects ofMaha-ya-na Buddhism and itsRelation to Hinaya-na 西元一九三○年)、《初期佛教的教团》(Early Buddhist Monachism 西元 一九四一年),但他主要的特长在於梵文佛教,故於西元一九三四年校订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订了《法华经》出版,此后继续校订含有《根本说一切部毘奈耶》及《三昧王经》的《吉尔吉特写本集》,当他在加尔各答大学退休之后,即任孟加拉亚洲协会的会长等职。
由於以上诸位大学者的薰陶之下,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辈出,俨然形成了一个加尔各答佛教学派。其中包括现任那烂陀大学巴利文研究所所长马克尔杰(Satkari Mukherj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Flux 西元一九三六年);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却(P. C. Bagchi),乃是着名的中央亚细亚考古学者;麦琴达尔(R.C.Majumdar)是专攻东南亚佛教史的学者。

与加尔各答大学同为佛教学研究之中心的,则为维湿瓦巴拉迪大学(Visa-nti Bhiksu)这所大学的特色,是以梵文与汉文佛典的研究为主。在巴咯却教授担任副校长期间,出有《二种梵汉语汇》(Deux-lexiques Sanskrit-chinois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的佛教圣典》(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八年)。另有萨斯特利教授(N. Aiyaswami Sastri)将汉文的《观所缘论》、《稻芊经》、《大乘掌珍论》、《十二门论》等还原为梵文。Santi Bhiksu Satri则将《发菩提心经》、《发智论》等还译为梵文。摩克波提耶(S. K. Mukhopadhyaya)教授校订了《三无性论》及《金刚针论》等书。帕罗塘(Pralhad Pradhan)教授校订了《阿毘达磨集论》,於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诃菩提协会,在鹿野苑设立出版社,将巴利语圣典,译成印度方言出版,该会僧侣会员的摄化对象,多为印度人及欧洲人,因其不乏饱学的比丘。
现在佛陀的祖国,已有几所研究佛学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Kashi Prasad JayaswalResearch Institute)、那烂陀的巴利文研究所(Na-landa Pa-li Institute)、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学等。
总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学的风气,已不寂寞,并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以上取材於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六九-二七六页)
教团的概况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虽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摄化方面,却尚不够理想。也就是说,知识的或学问的佛教,固然已经在上层结构的大学里生根滋长;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还未能够渗入印度人的社会,更未能够普及民间。纵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却不是真正的佛教。据朱斐的《空中行脚》三七页说:除了印度僧伽,现在锡兰僧十五人、缅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国及泰国僧各十人,信徒仅得四百万人。又据查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弥约二十多人,能够弘法的比丘,仅三、四人而已。这以印度人囗的比率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筑,现有印度的、锡兰的、缅甸的、日本的、泰国的和西藏的。中国则有李俊承居士捐资、德玉法师督建於鹿野苑的中华佛寺,由果莲比丘尼建於拘尸那罗释尊涅盘处的极乐寺,由永虔法师建於佛陀伽耶的大觉寺,由仁证法师建於舍卫国的华光寺,由福金喇嘛建於那烂陀的中华佛寺。
正由於佛教的教团,在印度尚极脆弱,目前急需展开佛教信仰的复兴运动,印度政府也有意协助。只是弘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为复兴印度的佛教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