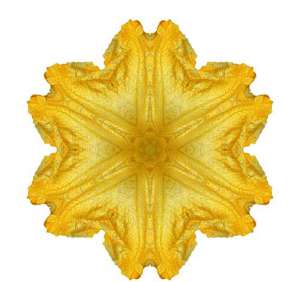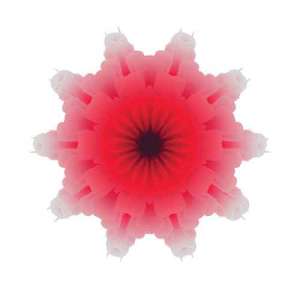从此岸到彼岸
发布时间:2019-09-21 09:57:18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
佛教在线讯 佛山因曾出土过三尊唐代的金佛,又名“禅城”。有禅之地,其意空灵。这儿的山水有几分仙气,民俗也充满了宗教意味。行通济,是佛山最具禅意的风俗了。
通济是一座桥。这桥非同一般,据说每年的元宵节,只要你在通济桥上走了一遭,就会安康幸福,无疾无忧。按当地人的说法就是:“行通济,无闭翳”。
这一风俗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了。它像一束古老的月光,穿越了漫漫时空,安详地照拂着尘世中的人们。通济桥始建于明代,最早是木桥。木易朽烂,所以它在明代就历经了三次重修。到了清代,木桥被改建成木石拱桥。建国后,它又脱胎换骨,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拱桥。从通济桥材质的变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进程,或者说我们是由柔软走向了坚硬。不管桥怎么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一直充当着诺亚方舟的角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桥上绵绵不绝的足印,就是人类祈祷的心声。
元宵节是我的生日。在北方,飞雪和寒流,通常是我生日的两道流苏。而在南方,斑斓的花树做了生日最天然的蜡烛,点燃这蜡烛的,是唱春的鸟儿那如火的目光。
此次在异地过生日,是为了参加“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的颁奖礼。当我坐在台下,聆听我喜爱的配音演员童自荣先生和姚锡娟女士朗诵我的获奖作品《花/子的春天》的片段时,我陶醉了。童自荣先生演绎的那个魅力非凡的独行侠———佐罗,曾是我少女时崇拜的偶像。是童先生的声音让法国的阿兰·德隆在中国家喻户晓。我在鲁迅文学院求学时,曾买过童自荣先生的诗词朗诵磁带。他的声音与另一位我喜爱的歌唱家的声音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极富磁性,在纯净中透着妖娆之气,刚毅而柔美,不可抗拒。这样的声音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颁奖典礼结束,晚宴后,与会的朋友们手持彩色风车,赶往通济桥。
天已黑了,乌云翻卷着,空气有些沉闷。虽然还没有到行通济的高潮上,但桥前已是万头攒动,交警在各个路口把持着,疏导人流。桥上灯火璀璨,人们除了拿着风车和风铃,有的还抱着一捆生菜,意谓“生财”。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阿婆,也有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娃娃。人们喜气洋洋的,怀着各自的期盼,缓缓走过通济桥。据说,行通济要从桥头一直走到桥尾,也就是由北岸直达南岸,中间不能折返,否则不吉利。桥长不过三十二米,若在平素,即便慢行,一两分钟也会通过了。但在元宵节的晚上,行通济,起码要花上五分钟,甚至更长。看来幸福是需要一步三叹的。

在摩肩接踵的人丛中,忽听周围的人说:上了通济桥了!我把风车举高,上了桥,也许是空气太闷,风车蔫头蔫脑的,并不旋转。我在桥上听不见流水,更看不见月光,感受到的只是无与伦比的喧闹。麦加的朝圣,曾屡屡发生踩踏事件。朝拜是神圣的,也是危险的,所以我留神着脚下的路。据说,行通济的时候,若是在心中许愿,会很灵验。我没有许任何愿望,在我看来,能够自如地走路,不论是什么样的路,都是福。桥,其实是人间的路上的一个破折号,在它下面,注定会缀着密密麻麻的人生注解。人实在是太多,我根本没有看清这桥的模样,就被人簇拥着,在朦胧的喜悦中过了桥。
说来奇怪,过了桥,天就落雨了。不过这雨轻描淡写的,只是寥寥雨滴,空气好了起来。起风了,风车乐了,那红色和金黄色的风轮在我眼前刷刷地旋转,五光十色,绚丽极了。从北岸到南岸,其实是从人生的此岸到了彼岸,未敢说把烦恼和忧愁一扫而光,但在万民祈福的时刻,我还是感受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感受到了超凡脱俗的快乐。
立地成佛者,从此岸到彼岸,只是一瞬;而苦苦修行者,从此岸到彼岸,则需百年。我有七情六欲,想必到达澄澈的彼岸,还有待时日吧。能够从通济桥上走一回,其实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提升,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省。我庆幸在我四十三岁生日的这一天,能在热闹中体味寂静之美,能在风雨中无悔地回顾从前。
元宵节的次日,我到珠江电视台录制“飞鸿茶居”的文化访谈节目,主持人对我说,行通济,如果连行三年,则会一生安泰。他问我明年和后年的元宵节,会不会再来佛山行通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我已经走了三次。元宵节的晚上,我现实地走了一回;过了桥后,我回望了通济桥,用目光又走了一回;晚上,我在睡眠中见到它,等于在梦想中第三次行了通济桥。所以,我已不需要我的肉身再去走两次了。
如此说来,从此岸到彼岸,是有多种的抵达途径啊。(信息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