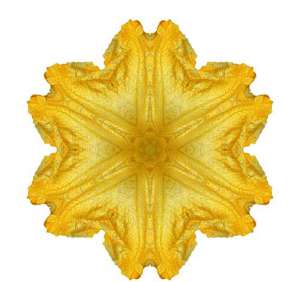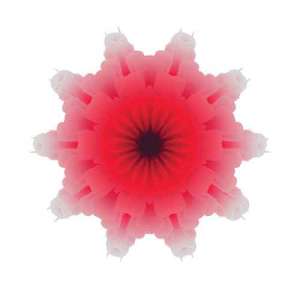佛、禅美学二题
发布时间:2019-10-12 09:53:26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佛教、禅宗有十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典籍中蕴藏十分丰富的美学资料,有待后人开掘。按“美”的本义来说,佛、禅都不可言“美”,因为“美”是由外部事物在眼睛中的视觉映象而发生,有形有色,言“美”,有悖于佛教的“四大皆空”论之“色空”。但是,佛徒们实在不能泯灭心中潜在的美意识,有时会在他们的言谈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对在他之前已译出经书的文字艰涩,十分不满:“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据他说,梵文的经书文辞是很美的;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1]
他批评的这种现象,后来很快就改进了,到了“中华禅”的时代,讲究文辞意味之美,虽不明言,禅宗之徒们可说是非常自觉,几有与诗人、文学家媲美的程度(有的僧人成为了优秀诗人,如皎然、寒山、拾得等)。据《五灯会元》卷一所录,六祖慧能评师兄神秀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曾有言:“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原话中是否确用了“美”字,当可怀疑,但撰《五灯会元》的宋代普济僧人未回避“美”字,表明美意识没有在他的心中泯灭。
佛、禅学理渊深,非我等凡俗之人可窥其堂奥,而其美意识因有“色空”之戒,更隐藏深深,要较为全面透彻地了解,似乎不大可能。著者浏览若干佛、禅典籍,仅就直觉所感美者,于无际丛林中拾叶若干,现列两题如下。
一、“妙悟在于即真”
“悟”在先秦典籍中早已出现,今文《尚书》里,周成王临死前所作遗嘱《顾命》篇,有“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之句,“悟”有觉醒、理解之义,后引申为受到某种启发,心眼豁然贯通,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佛学就是欲使世人蒙昧的心灵觉醒,释迦牟尼苦修多年后,某日独坐一菩提树下,忽然有悟而得“道”。将“悟”字引入汉译佛经,最早可能出现于鸠摩罗什所译之《法华经》:
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方便品》)
这里讲的是“悟佛”,与前章谈到的“感物”说有根本的区别。儒家的“感物”与道家的“游心”,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心之外有物的存在,外物通过五官感觉入于心,或心主动入物而“神与物游”。佛、禅在“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与儒、道截然不同。佛禅以“心性”为人的本体,除了“心性”是真实的存在,一切外物皆为虚为幻。据六祖慧能说:“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稍带有物质性的便是“心地”,心如大地一样生长草木万物,这就是所谓“心生万物”,“心含万法是大”。慧能为徒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时有云: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引六祖语,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船若品》、《决疑品》。)
如果以“境界”言,“心地”是绝对的大境界。《淮南子》言所谓“无外之境”,实指空间与时间无限的宇宙,本于庄子与宋全+开、尹文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说,对于“心”来说,是一个“至小无内”的内宇宙,与“至大无外”的外宇宙融通一体。佛、禅则只承认一个内宇宙,这个内宇宙即是慧能所描述的,一个虚空无物亦无情的“世界”。他们也讲“所见”、“所闻”、“所触”,但对闻、见、触不能有“分别心”,即不能分析思考,一旦心有了“分别”,外物就侵入了澄明虚静的心地,本体心性就被破坏了。当然,佛禅僧徒们都生活在物质世界,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束缚他们的身心,中国早期的佛徒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慧远同时代的僧肇说: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不真空论》)
这就是说,在万物之前,要主观地以万物为“虚”,看见等于没有看见,不以万物感于心、留于心。玄学家王弼说“应物不累于物”,佛家则是根本不应物,绝对不为外物所扰,我前无物(道、玄是“物前无我”),即是“心无”。后来的禅宗也接受了这一说法,天台惟则禅师说:
天地无物也,物我无物也。虽无物也,而未尝无物也。如此,则圣人如影,百姓如梦,孰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五灯会元》卷二)
他们确实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习佛习禅要“心无”,而心之外,物又未尝无,如何使心性返归到绝对的本真状态?所谓去“有”,那就要让自己的“心地”净无一尘,连所谓“圣人”也不过是一个影子,一切凡尘之物皆如梦中所见,一片幻影,恍然出现,恍然消失,无“始卒之端”,无生死之别。如何入“无”而臻至佛的境界?修行之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凭自己的心力,即“内功”,摒弃在“万物未尝无”的世界里“感物”的干扰,“悟”入永不会醒来的梦境中。鸠摩罗什译经班子成员之一的僧肇,首先提出了“妙悟”说:
……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同我则非复有无,异我则乖于会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间矣。何则?夫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余;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至能拔玄根于未始,即群动以静心,恬淡渊默,妙契自然;所以处有不有,居无不无。居无不无,故不无于无;处有不有,故不有于有。故能不出有无,而不在有无者也。[2]
这“妙悟”的根本之义,就是彻底消除对有、无的“分别心”,“异我则乖于会通”是一个关键句。要消除有无之界,对一般人来说,是不易跨越的铁门槛,对“至人”来说,“虚心冥照”是一个大前提,这就是心已“本来无一物”(道家讲“致虚极、守静笃”只是强调“无欲”而观万物自在之态,不是“无物”之观),因此,物之“有”即使入于心中,也顷刻化于“虚无”心地而无形无迹,“六合”、“万有”、“群动”皆消融于“恬淡渊默”的空无之境。设想一下,如果去分别“六合”之大小上下,“万有”之多少优劣,“群动”之快慢静躁,心还能虚静吗?僧肇说“妙悟”之“即真”,“即真”就是直达心性本体,“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超出一切对立、异同分别之上,作天、地、我、物“彼己莫二”之“齐观”。这实质上是彻底反理性,也是反思维,后来禅宗三祖僧粲在《信心铭》写道:“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目。”(《五灯会元》卷一)也是发挥反思维之道。
“悟”,从常人的心理活动而观,实际上是思维的升华,进入超思维的一种精神飞跃。僧肇言“妙悟”,是以“至人”之悟为高标,实际上,佛禅弟子们并不是个个都能一“悟”而“妙”的,他们之中有的天分很高,思维方法对路,往往很快就能跨越“有、无”这个铁门槛,有的人则要经过长期学习佛理,修心炼性,才能逐渐开悟,因此,又出现了“渐悟”与“顿悟”之分。与僧肇同时,也是罗什译经合作者的竺道生,论述由“渐”而“顿”说:
盖真理自然,无为无造。佛性平等,湛然常照。无为则无有妄为,常照则不可宰割。寻夫本性无妄,而凡夫因无明而起乖异;真理无差,而凡夫断鹤续凫以求通达,是皆迷之为患也。除迷去患,唯赖智慧,而真智既发,则如果熟自零。是以不二之悟,符彼不分之理,豁然贯通,涣然冰释,是谓顿悟。[3]
这里实际说的是,本来人人都有佛性,如果“本性无妄”,都是可悟入的,但有的人却会不自觉地“妄为”,那就是起“乖异”的分别有无、是非之心,乃至有以长续短的愚妄之举,这就是“多言多虑”,因此,他必须“除迷去患”才能接近“绝言绝虑”的境地,一朝修炼到家,“真智既发”,顿然而悟,那就瓜熟蒂落般地一瞬间自然而然圆满完成。“真智既发”实质就是日常思维的飞跃、升华。“渐悟”还在思维过程中,“顿悟”则是升华的一瞬间,“渐悟”与“顿悟”有一个时间差。“顿悟”与“妙悟”,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真”为最高境界,是“真智既发”之果;而“渐悟”,因“真智”尚未发到极致,所悟之果尚未成熟,所以与“顿悟”有高下之别。五祖弘忍两位弟子——神秀与慧能,可作为“渐悟”、“顿悟”的典型范例:
神秀到五祖弘忍门下,“誓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识之,深加器重”,日长月久,已取得“上座”弟子之位,似乎成了禅宗衣钵的当然接班人。一日,五祖“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弘忍门下七百余僧,大家认为,上座神秀学通内外,“若非尊秀,畴敢当之?”神秀“窃聆众誉,不复思维”,便在廊壁上写下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读后,基本是肯定的,说“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且对弟子们“各令念诵”。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从广东远道而到五祖门庭不久的一位年青人——尚未正式出家又不识字的卢慧能,其时“服劳而杵臼之间”,闻说神秀之偈后,认为“了则未了”,请人代笔,在神秀偈旁写下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比照而读,两偈的高下不言自明了。神秀违背了“明理不可分,悟语极照,以不二之语,符不分之理”(慧达《肇论疏》)的最高禅理,第一、二句皆是“有二”之语,即以自我的“身”与“心”同客观存在的“树”与“镜”互拟;第三、四句则落“渐悟”之义,以“时时勤拂拭”的主观努力逐渐消除心中的“尘埃”。慧能则针对神秀之语一一否定,“本非”、“亦非”正是以“不二之语,符不分之理”,“本来无一物”表现了他的顿悟:“身”与“心”、“树”与“镜”都是“虚无”,何“尘埃”之有?慧能彻底回归于心性本体。对照之下,弘忍也似乎到此时才发现神秀偈的“真智”未发,私下里对神秀说:“汝作此偈未见其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物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这显然是比较了两偈之后作出的评论,其说到“无上菩提”即佛之境界,实是对慧能偈的高度评价,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之语。以现代哲学观而言,慧能之偈与弘忍的说教都属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而神秀尚未及此,因“万法”在他心中有“滞”,只能说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五祖将衣钵传给了慧能,后来,慧能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念了一偈: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顿悟华情己,菩提果自成。(《五灯会元》卷一)
似乎是回顾他得到衣钵的原因和经过,所谓“诸种”,是指智慧的种子,“普雨”是言佛之“法雨”,“华情”是指眷恋于物质世界之迷离妄执,由于“顿悟”排除了一切迷患异我,“果熟自零”终于获得了无上智慧。他还嘱咐学生:“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慧能得衣钵后在南方传法,弟子众多,用“顿悟”之法传授弟子,因此南宗又被尊为“顿教”。他的弟子们对“顿悟”之后获得那种身心解脱感、精神自由、愉悦感,往往不回避美的描述。慧能第三代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在回答学生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时,先对“顿悟”之法作了扼要的阐释:“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万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接着便对进入“顿悟”的境界作了描述:
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五灯会元》卷三)
后两句显然有美的感觉。第五代弟子圭峰宗密禅师,对“顿”、“渐”之悟作了比较,运用喻象进行表述:
真理即悟而顿圆,妄情息之而渐尽。顿圆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已全。渐修如长养成人,多年而志气方立。(《五灯会元》卷二)
“顿悟”如可爱的婴孩,有纯洁、天真、活泼之趣,“渐悟”则显老成、稳健之态。后来又有禅师用自然景物来比喻“顿”、“渐”,前者是“月落寒潭”,后者是“云生碧汉”。寒潭之月已非天上之月,虚而不可实求也;云生于碧空而在碧空,可似观而见,非虚而尚实也。他还用一首五言诗表“顿悟”的心境:
冷似秋潭月,无心合太虚。山高流水急,何处驻游鱼?(《五灯会元》卷十六)
第三句是言“顿悟”者彻底克服了迷妄,如不能映月不能驻游鱼的急湍流水已化为平静一潭,澄明透彻,映月清朗,游鱼自在。著者在已读到的“顿悟”诗中,出自吾乡杨歧方会禅师门下的舒州白云守端禅师所作一首,给我留下心与目皆感其美的印象。其诗云: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五灯会元》卷十九)
最后一句所谓“照破”,实谓在我明珠般的心之光芒照耀下,山河大地通体透明,“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使我联想李商隐“蓝田日暖玉生烟”的优美诗句。方会禅师听他诵毕,“笑而趋起”。这是会心的微笑,守端以为自己所言不当,“愕然,通夕不寐”。第二天,方会对他说:你有一筹不及我。守端“复骇”曰:“意旨如何?”方会说:“渠(我)爱人笑,汝怕人笑。”于是,守端成为方会的首座弟子。
佛、禅之“悟”,由僧肇的“妙悟”而至竺道生的“顿悟”,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佛学界,到了唐代才由少数诗僧引入诗歌创作领域,如中唐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述自己作的一首诗中,就有“东风吹杉梧,幽月到石壁,此中一悟心,可与千载敌”之句,将“悟”与“心”联系起来。皎然是以思维的升华而言“悟”的,因为他还有作诗须“苦思”之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取境》)从“苦思”到最后有似“不思而得”,正是一个升华过程,这个说法,容易被诗人接受。
南宗“顿悟”说及其“悟”之典型范例广泛传播,到了宋代尤盛,更多的诗人和诗论家发现,“顿悟”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唤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于是积极接收到两宋的诗学理论中来。先是在不少的论诗诗中有强调性的表述,如被划入江西派的韩驹《赠赵伯渔》诗结论性的四句:“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龚相《学诗诗》之一:“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占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连陈师道这样的“苦吟”诗人,也说写诗是“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已,故必悟”。最著名当然是以禅喻诗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大谈“妙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而他最欣赏的“透彻之悟”:“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实质就是“顿悟”。严羽的“妙悟”对诗人而言,一悟之后,当然不是“万法皆空”,不能是“无一物”,而是使其审美对象变得“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现实世界中的实景实物,转化为诗中的虚物虚景,即诗人情思化的美物美景。关于禅悟与诗悟的同与异,严羽之后,明朝诗论家胡应麟论曰:
严羽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捧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4]
清初周亮工编《尺牍新钞》收录了一封谈诗与禅的信(陈宏绪《与雪崖》)[5]立于诗之本体作了“相类而合”与“淄渑之别”的分析:
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而无取于辟支声闻小果。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然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性。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诗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之空华阳焰,漠然不以置怀,动于中则深以为戒,而况形之于言哉!
这个比较分析是正确的,禅悟要排除感情,排除得愈彻底(即慧能说的“华情已”),方可“顿悟”,否则便是“渐悟”或未悟。因此,那些禅宗高僧悟道的偈颂禅诗,蕴含的是佛理禅趣,而诗人则是“通灵感物”而悟,有强烈的情感驱动,悟的结果,不是“恬淡渊默”的“妙契自然”,而是如司空图所说“生气远出”的“妙造自然”(《二十四诗品?精神》)。严羽标举“妙悟”,通于西方诗学的“灵感”说,中国诗学的“灵感”理论自此而基本定型,佛、禅有先发、启迪、助成之功,功不可没。
二、“以指指月,而月非其指”
佛学禅理中,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现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不用语言文字进行传授,但是却有大量的佛学典籍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佛徒们学习之后,自己也著书立说。禅宗虽少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高僧们“上堂”与平时师生问答的话语,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号曰“语录”,广为流传,怎能说是“不立文字”呢?原来,“不立文字”是指他所悟入的那个“玄道”,其“道”本是“空无”,“实相无相”(据《教行信证证卷》言:“无为法身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法性,法相即是真如”),“无相”,当然不能以言语文字进行摹拟性描写。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不能见诸于文字描述的。竺道生在《妙法莲华经》中说:“夫至象无形,至音无声,希微绝朕思之境,岂有形言者哉?”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所用的语言文字起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看鸠摩罗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关于“明实相离合”的一段话:
汝于摩诃衍中不能了,但著言声摩诃衍中诸法相实。实相不可破,无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诃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时微细,有明眼人能见,指示不见者。此不见人,但视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语言:“痴人!何以但视我指?指为月缘,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者非实相,但假言表实理,汝更著言声,暗于实相。[1]
这段话是设想有一个“汝”想用实在的言语描述、阐释佛家经典中的“诸法实相”,“实相”本“无相之相”,你从何说起又如何说呢?若可说破,佛祖早就说了,能够说破,任何佛典也不是佛典了。《三昧经》的作者为说明佛典的作用,还是用了一个比喻;以指指月。月在虚空之中,初生之月更是细微难察,有人指给你看,你应该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你没有看见,便老看着那手指,岂不是把手指当成了月亮。这就是说,所有的佛学典籍都是指向佛的手指,手指不是月,语言文字讲述的佛理不是佛,欲悟佛而去佛经中寻找佛何在的人,不过是在反复打量那个指头而已。
“以指指月,而月非其指”,即“实相离言”之意,与罗什一道翻佛经,并被称为罗什门下“八俊”之一的竺道生,找到了中国式的解释。据《高僧传》记载: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意。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原来,类似“指月”说,中国早就有了,那就是《庄子》的“语不足贵”、古人之书为“糟粕”(《天道》),而有“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说(《外物》)。到三国时代,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发挥出学理严密的“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换成佛家语来说,应该是:离指而见月,得月而忘指。据说,竺道生就是因此而“校阅真俗,研思因果”而发明了“顿悟”说。
由“指月”而“顿悟”,实开后世禅宗之端绪。而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更是将“指月”说发挥得淋漓尽致。慧能三岁丧父,出身贫苦,不识字,却能听人读《金刚经》、《涅槃经》,且有所感悟,有人问他:“字尚不识,曷能会义?”他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他认为,佛法大意不在佛经,不能迷于“指月”之“指”,佛也不是释迦牟尼一人,“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按他的说法,“月”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他的二代弟子马祖道一禅师明确地说:“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我们读《五灯会元》及各种禅宗语录等书会发现:“以指指月”在他们那里,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取消手指一定的指向或干脆砍掉手指;二是将“月”以种种意象化呈现,似指非指,非月似月。后者,蕴含了禅宗丰富的美意识。
“如何是佛”、“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是禅宗典籍中频繁出现的三个问题,或是初入禅门的人想直截地解开自己的迷惑,或是高僧之间互相考问以察对方功底的深浅。这三个问题,无疑都是“手指”。有功底的禅师,从不直接回答,或是答非所问,或是沉默不言,更有甚者是“棒喝”提问者。“如何是佛”,从无人答西天某佛祖,出人意外的是:“麻三斤”、“洗钵盂”、“大罗卜头”、“青州布衫”、“干屎橛”等等,几乎是见什么便可说什么,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有意说些大不敬的话,这种种貌似胡闹的所指,无非就是表明心外根本无佛。答得较为文明的,如龙境伦禅师答“如何是佛”:“勤耕田”。问者说:“不会”,又补一句:“早收禾”。沩山灵佑法师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大好灯笼。”赵州从谂则答:“庭前柏树子。”青原行思被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反问:“庐陵米作何价?”等等,千问千种古怪答案。最有趣的是“棒喝”,请看临济义玄接引弟子的一段记载: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说:“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失性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大意,三度蒙他赐杖。”(《临济录》)
义玄竖起拂子,犹如伸出一指,可是僧不明其指,一问再问,所以被打(如果僧拔去义玄手中拂子远远抛开,或许就不被打了)。有个俱胝僧人,每逢有人问诸如此类的问题就竖起一个指头,常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僧人也学着竖指头。有一天,俱胝暗藏利刃叫来小僧人,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小僧人照例伸出一个指头,俱胝竟出刀将其指头砍了,小僧人吓得拔腿便逃,俱胝追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他欲伸指发现指头没了,瞬间“顿悟”。禅师之“指”仅仅暗示一个向度,后来不少禅师就青原行思的“庐陵米价”话头作偈,稍稍透露此“指”之意,录四首于下(选录自宋法应元普禅师编《颂古联珠通集》卷九):
庐陵米价逐年新,道听虚传未必真。大意不须歧路问,高低宜见本来人。(黄龙慧南禅师)
庐陵米价越尖新,那个商量不挂唇。无限清风生阃外,休将升头计疏亲。(白云守端禅师)
庐陵米价播诸方,高唱轻酬力未当。觌面不干升斗事,悠悠南北漫猜量。(长灵守卓禅师)
庐陵米价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绣出鸳鸯任人看,无端却要觅金针?(鼓山珪禅师)
佛法不可言解,能言解者不是佛法,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四首偈都在暗示:佛向内心求,无需“觅金针”。
“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一个人回家,难道还要问路怎么走?有些文学修养特高的禅师,为回避直接回答,运用诗的意象化语言营造迷离恍惚的意境,呈现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悟道氛围。天柱崇慧禅师的答问很有代表性。学生问“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他第一次回答是没来就没来,现在还问什么?学生不解,还“乞师指示”,他没有打,说了:“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可能有自然而来,自然而去之意)学生才不语。此录他以意象化诗句答问,供读者欣赏:
问:“如何是天柱境?”
答:“主簿山高难见日,玉镜峰前易晓人。”(陈按:巧用山名。“主簿”,本为主管文书官。以此官名一座山,想此山亦有据案弄书之态。)
问:“如何是天柱家风?”
答:“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
问:“如何是道?”
答:“白云覆青嶂,蜂鸟步庭花。
问:宗门中事,请师举唱。”
答:“石牛长吼真空外,木马嘶时月隐山。”
问:“如何是僧人利人处?”
答:“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问:“如何是天柱山中人?”
答:“独步千峰顶,优游九曲泉。”
问:“如何是西来意?”
答:“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御花绿蕊间”(《五灯会元》卷二)
他的应答与所问内容可能有些内在联系,但均升华到诗的境界,如果确未经过后人的修饰,崇慧应是一位高明优秀的即兴诗人。这样的诗人在禅宗门中大有人在,萍乡杨歧方会禅师某日上堂:
“杨歧乍住屋壁疏,满床尽布雪真珠。缩却项,暗嗟吁。”良久曰:“翻忆古人树居。”(《五灯会元》卷十九)
下雪天雪粒穿过破屋,冻得缩颈暗叹,但忆起了释迦牟尼,居坐菩提树下而悟道,自然就心境开朗了。他的三传弟子大平慧懃禅师,一日上堂即诵:
金乌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无穷游子不归家,纵归只在门前立。门前立,把手牵伊不肯入。万里看看寸草无,残花落地无人拾。无人拾,一回雨过一回湿。(《五灯会元》卷十九)
他说:“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这是一首意味幽深的诗,也是“密诗”,我们只能体味到在时光流逝中的一个空寂世界,或许也表达了出家人皈依佛门四大皆空的心境。
“以指指月”的神宗心法,传到了诗人、艺术家手里,立即成为了审美的指向,他们恍然明白,在艺术领域内,那个“指头”是什么,“月”又是什么,南朝齐代画家、画论家谢赫有一评画之语,曰:
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古画品录》)
这实际上就在区分“指”与“月”,“骨法”用笔与“体物”皆是“指”,“象外”之“精灵”便是“月”。禅宗“极象外之谈”,到南宗流行的唐代,“指”与“月”的关系便很自然地转换成了诗中的“象”与“境”的关系,诗歌理论与创作都很有造诣的释皎然,在《答俞校书冬夜》诗中有云:
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镜。真是在杳冥,浮念寄形影。
以“月”为“禅中境”,看来是他作为方外人士的一种自觉,《答郑方回》亦云:“……琴语掩为闻,山心声宜听。是时寒光彻,万境澄以净。”《宿山寺中见李中丞》又有:“偶来中峰宿,闲坐见真境。寂寂孤月心,亭亭园泉影。”如此,则形影意象便是进入“禅中境”、“真境”也是诗境之“指”。从诗的创作角度言,皎然有“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的“取境”法则。作为诗人,创造供人欣赏的美的诗篇,不能如禅宗之偈那样仅仅是自悟自了,为了让凡俗之人也能领略诗境之美,必须有可妙用之“指”,不能不特别重视语言文字和形象意象的运用与呈现,所谓“采奇”、所谓“状飞动”,都是为强化“指”的功能,他甚至提倡诗要“苦思”,“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
皎然之前,王昌龄诗境理论已经创立,“唯识宗”等佛学理论对其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王昌龄而后,诗境理论的发展,则明显受禅宗的影响日深,一批诗僧更在其中推波助澜。中唐诗人权德舆一篇《送灵彻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不但描述了灵彻法师诗歌境界“风松相韵,冰玉相叩,层峰千仞,下有金碧”又“淡然天和”之妙,而且以“常境”对诗境理论有新的发挥。刘禹锡是一位与禅宗人士交往甚密的诗人,他的诗集中专编“送赠”诗一卷,为杨歧甄叔等禅林高僧写过传记和塔铭。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诗“境”生于“象外”之说:
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象”非“境”,“境”在“象外”,这不就是“月非其指”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吗?佛、禅“指”、“月”说,其潜在的美学意义将在诗境理论中充分地发挥,在诗人创作实践中其“指”有无穷的妙用,无须我在此赘述了。

【参考文献】

[1]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 涅槃无名论[A].全晋文[M].卷一百六十五.
[3] 竺道生论“顿悟”原文已佚,汤用彤先生搜其遗文,此据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朝佛教史》所载文字。中华书局,1955.658-659.
[4] 诗薮[M].(内篇卷二).
[5] 陈良运.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C].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