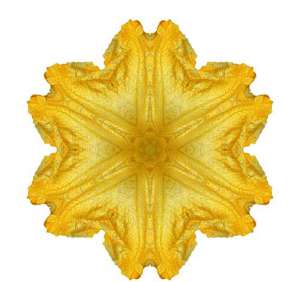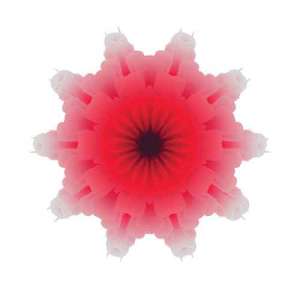克孜尔石窟:在遥想与走近之间
发布时间:2019-11-01 09:53:53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他的静默是向下的。他的姿态向下,他的目光向下,他的神情像是在亲善地微笑,却感觉得到他的神思飞向了那些洞窟、那些经文、那些日复一日的冥想。远处土黄色山上的著名洞窟成了他的背景。他也成了关注那些洞窟的目光的第一落点。
一个对佛学所知寥寥的人来了。如同所有想来这里的人一样,我是被洞窟里那些即便是横遭浩劫而残存的美丽依然令世人炫目的壁画吸引而来的。
遥想
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距离我们有千年之遥。当我们沿着古老的龟兹壁画,向上追溯,以抵达时光的另一端的时候,需要怎样的心智、体悟和想象力呢?
这里的一切对于我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有着意想不到的整齐和有序。不由得想起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当你走进去,要穿越一段古旧的民宅,与仿佛古今贯通的居民们擦肩而过,甚至会看到德国强盗冯·勒柯克住过的房子……我们就在现实与远古的交替中,在真实与梦幻的转换中走过摇摇晃晃的木梯,走上几乎被破坏殆尽的洞窟。
在这里,你可以直奔主题。在这里,你可以在白色的日光下径直踏上一段阶梯,通览克孜尔石窟的全貌。
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石窟形制主要有四种,即方形窟、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壁画内容主要反映小乘佛教“惟礼释迦”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中心石窟,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石窟是古代龟兹人民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艺术的基础上,适应当地的地质环境的特点而开凿的,也被称为“西域模式”,是古代龟兹人民的一项发明和创造。
克孜尔石窟(亦称千佛洞)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即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这一载体,进行传播、交流、交汇与渗透,完美结合的唯一体现。它代表了古代中亚和西亚艺术发展的顶峰,曾对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艺术的东渐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起始点。著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曾经指出:解开敦煌文化之谜的金钥匙就在克孜尔石窟。
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因素让克孜尔石窟饱经沧桑。站在残缺不全的壁画面前,我们想像着当年镀了金箔,绘有青金石、孔雀石等明亮色彩的绚丽壁画填满洞窟、或大或小的塑像栩栩如生的景象,想像着好似被漫天繁星般的壁画所簇拥了的繁茂,那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呵。
当我们的目光循着壁画的线条细细解读的进程在残缺的边际戛然而止的时候,当我们驰骋想像的翅膀飞向苍穹却被迫折回的时候,一声叹息,轻轻划过时空,为那逝去的美丽献上不落痕迹的挽歌。
走近
得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李瑞哲博士将给我们作讲解,我们兴奋地去找到他。他刚整理完院子里的东西,满手都是绿色颜料。
那一天是5月27日,我们与李博士一起坐上电瓶车,驶向石窟西区。再攀登一段回旋曲折的阶梯,气喘吁吁地抵达我们要观看的第一个石窟8号洞窟。
走进去,一片阴凉,立时消解了刚才在烈日下攀登的劳累与灼热。满眼壁画很快将我们带入那些佛经故事。那些佛经故事原本枯燥,如今却在一幅幅美丽壁画里生动起来,让人若有所悟。在这里,又一次听到德国人冯·勒柯克的名字,墙壁上一块块被生生剥去的印痕还那么刺目,我的心又一次像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时那样疼痛。
克孜尔石窟目前所遗存的约10000平方米的壁画,主要分布在近百个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中,壁画内容有佛像,菩萨像,天龙八部,天象图,佛经故事,说法图,动物,山水,树木,装饰图案,以及供养人像等。其中佛本生故事画种类共计135种,因缘故事画70余种。近千幅佛本生、因缘故事以独特的菱形形式分别被描绘在中心柱窟的顶部。
精致的佛经故事画,数量与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中都是罕见的。
开凿较早的特窟38窟,听李博士说门票100元才能进来———是礼拜窟,风格明亮,成熟的画风与8号窟一致,也称为伎乐窟;两侧壁描绘的两列天宫菩萨乐舞组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前壁所绘游戏坐姿状的思维菩萨像,仿佛正在沉思着什么。据说坐落在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青铜塑像就是参照了这种姿势牞属于第二种印度———伊朗风格的壁画。
李博士说,直到公元七世纪中叶以后安西都护府从交河移往龟兹时,克孜尔石窟才开始出现了约10个左右的绘满千佛的洞窟,反映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内容。
17号洞窟也是一个中心洞窟,42个菱形格就有42个故事,我们也仿佛进入了故事的海洋。十分有意思的是,有一幅画,一个僧人正在打坐,头顶上已然小鸟做窝,三只小鸟怡然自得,全然不知僧人因怕惊走小鸟,一动不动,已是骨瘦如
柴……对于万物生灵心存一种悲悯之情,何尝不是时至今日人类都必须努力学会的一门功课呢?
克孜尔石窟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安史之乱”,唐朝中央政府为了平乱,无暇顾及西域,使得突厥、吐蕃相继侵凌,造成龟兹地区社会动荡,龟兹佛教也由此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公元十世纪,随着伊斯兰文化越过帕米尔高原向东传播,克孜尔石窟逐渐被废弃,并遭到较大的人为破坏,壁画局部造成较为严重的损毁。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外国探险队不断在龟兹地区进行探险活动,致使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壁画遭到严重损坏,大部分洞窟内的精美壁画被野蛮地盗割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运抵德国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就有328平方米。许多洞窟的壁画上残留下斑斑刀痕,遗存壁画的病害侵蚀进程也加速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脸庞晒得黝黑的龟兹石窟研究所副所长徐永明。他手指着洞窟向我们公布了一个消息:他们把流落海外的克孜尔石窟珍贵壁画拍成照片,共有60幅,集中在谷东区165、166、167洞窟、谷西区34、43窟5个洞窟向游人展示。
这样一来,当我们面对那些残破的壁画时,心里的缺憾或许可以稍稍得以弥补。
醒省
环顾克孜尔石窟,土色的山体,是一种表面的干涸,暗凉的洞窟,是一种内里的浸润;而那一汪泪泉,淙鸣作响,让我们恍惚又听到龟兹古乐的遗韵。
克孜尔石窟何尝不是一串串错落起伏的韵律,拨击我们的心弦,挑起千重滋味,万般情怀。

我在想,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流传至今,都是有对一种人类基本要义的认同才得以传承,宗教的产生与延续,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甚至对于人类种族的繁衍都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的。站在石窟里,面对壁画,当你看到一个人为了将落难中的人们带出黑夜,不惜点燃了自己的手臂当作火把;当你看到一只猴子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安全渡河舍身做桥;当你看到鹿王为了解救众鹿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你都会被这种献身精神所感动。这种献身精神,人类已经洞悉它具有的意义非同寻常,所以,在洞窟壁画里才得以反复表现。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佛教在表现这种极其严肃的教义的时候,用了许多娱乐的形式:丰满的歌伎以其绚丽的服饰、妖娆的舞姿抓住人们的眼球;美丽的画卷里甚至有被称作“东方维纳斯”的胁侍菩萨,她那浑圆的脸庞、肩臂,飘逸的衣饰,令人迷醉。
如今我们在仰视这些壁画的时候,还能想象得出当时裙裾翩飞、仙乐飘飘的景象,可谓“声声龟兹乐,翩翩胡旋舞”。就在这种美得飘飘欲仙的感受中,严肃的教义直抵人心。
克孜尔石窟壁画在人物造型方面,从解剖学的角度看,科学准确地把握了所表现的人体结构,并采用色彩明暗晕染技法创作出凹凸的形体造型。这一独创的西域龟兹式凹凸画法,曾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中引发了一场大革命。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其深厚的龟兹民族文化底蕴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原汉地艺术以及印度艺术、希腊艺术、波斯艺术等多种外来文化养分,大胆创新,创造出独特的“西域龟兹艺术画派”风格。这一历史创举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所使用的矿物质颜料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依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成为研究中国传统重彩画(岩彩画)的“活化石”和中国艺术的典范。
此刻,我在想,当年,西方强盗忽然发现这些坐落在龟兹古国的浩大洞窟的时候,站在这些精美的壁画面前,一定是先被古老的四大文明在此交汇碰撞所迸射的光芒所震惊所震慑,继而才萌生窃取的念头,那是想把珍宝据为己有的一种盗贼心理。
走出洞窟,古老的壁画之美并没有随着光天化日的出现而消弭,反而越发生动了起来。这一回,我们是从洞窟走向鸠摩罗什。此时再看鸠摩罗什,他的眼睛若有所思,又深不可测,洞窟壁画所萌生的震撼,忽然就在他眼前化为了感动。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佛教徒的感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醒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