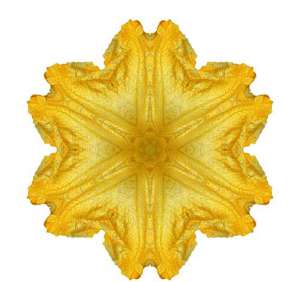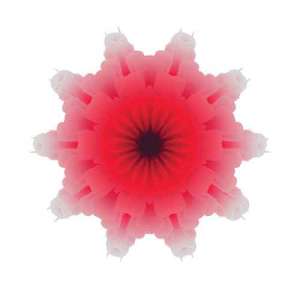净慧长老修行证道,弘法济世的一生
发布时间:2019-11-07 09:55:48作者:阿弥陀经结缘网
净慧法师(1916-2001),现代高僧大德。单字宽,俗名楼明达,小名根发,浙江象山石浦镇人。从1932年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起,从此在寺内共修持70年,任维那。
法师出生于一个虔信佛教的家庭。母亲怀他的时候,就不吃荤腥,是胎里素。法师小时候就深具慧根,自幼随母茹素烧香礼佛,敬信三宝,怀出世之志。
14岁那年,法师投苏州八塔寺,礼授松法师的徒弟黄岩多福寺从参法师座下披剃,法名净慧。旋至苏州报恩寺为茶役。1931年,又返石浦西龙庵潜修。翌年2月,至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台宗僧人,那一年净慧16岁。当时,台宗名宿静权大法师正在国清寺创建天台山佛学研究社,净慧得以亲近静权大法师,受其亲炙,研习天台教观,并随侍协助静公创建天台宗佛学研究社,使之解行精进。1941年慧莲和尚请为国清寺副讲。期间习天台教观及《妙法莲华经》、《楞严经》、《地藏经》、《阿弥陀经》等经。深得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之旨,乃笃信净土、专念弥陀。
1957年赴北京中国佛学院(首届)深造,系统学习天台教观和佛教知识。三年学成归寺,1959年回国清寺至1968年期间,历任副讲、主讲、修持股长等职,被澹云和尚请为首座,为主讲法师。1984年,为培育僧才,国清寺恢复天台佛学研究社,师以古稀之年任主讲。法师几乎每天坚持在妙法堂讲经,并于每年七月的佛欢喜日,宣讲《盂兰盆经》。
净慧法师以《妙法莲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为榜样,视一切众生为佛,特别重视自身的修持实践。在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课余时间,他巧把尘劳作佛事,自愿发心,每天打扫学院厕所。在国清寺教育僧才时,他身教重于言教,经常教导学僧要先学会做人。
净慧老法师年青时即讷于言、慎于事,中年以后,更是虔诚礼诵、阐讲《妙法莲华经》、《楞严经》、《地藏经》、《阿弥陀经》等法门典籍。教依天台,行归净土,坚持弘宗演教、台净双修。他解行并进,生活清苦,戒行严谨,广行布施无论贫贱,平时以节衣缩食所得经常普济有情。他爱国爱教,作育僧才,上弘下化,助印佛教典籍,以启群萌,醒悟众生。他深得止观之幽玄,闭门不出而潜修,晨昏苦切,无有懈怠。70余年常在定中,为众所钦仰,是台宗耆宿,法门长老!
净慧法师在少年时期,就爱好梵呗唱念,除了学会五堂功课以外,特别精通《水陆仪规》。天台山佛教可唱诵的经文约95篇,其中赞偈类22篇、朝暮课诵39篇、忏类9篇、瑜伽焰口9篇、水陆法会16篇(含乐器曲牌)。但由于缺乏文字资料,在民国之前,天台山佛教音乐无明确传承谱系。1932年(民国21年),净慧法师根据寺内高僧和各寺大德的口传内容,重新搜集整理多种忏法,终于使唱诵又有新的传承法系,延续至今。
净慧法师在水陆、焰口和经忏唱诵中,经过几十年的磨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听到过净慧法师唱诵的人,都无不被他那无比清越纯真的童子音所感动,在他的唱腔中没有一丝杂音,充满了清净和慈悲,超凡脱俗,有如天籁。这是一种真正的出世梵音,会令人情不自禁地流下忏悔的眼泪。
净慧法师以提携后学、培养弘法人才为已任,坚持不懈讲经说法,除了毫无保留地向年轻僧人传授开座讲经的仪式和说法的技巧外,并创造条件让学僧上坛讲经,自己旁听讲解。有时自己生病不能行走,就让侍者抬着到妙法堂听学僧讲经,然后进行剖析和引导。有一次,由于寺里事务繁忙,只有一二个学僧来听讲,净慧法师仍然照常开课,认真讲授。他说,只要有一个学僧来听课,我就要坚持上课,培养佛教人才是老僧的责任。
临终前,老法师仍念念不忘弘法利生,在弥留之际,他还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去妙法堂讲经、我要去妙法堂讲经
净慧法师身材瘦小,清静慈祥。由于长期缩衣节食,晨昏苦修,加上文革期间的摧残,落下了严重的胃病。1996年又不慎致跌,几乎半身不遂。但是病魔丝毫不能动摇他修学的道心,他将病痛作锤炼,内心安然受用,勇猛精进,每天不仅坚持讲经弘法,还坚持上殿过堂,参加早晚功课,主持寺内法事。做功课时净慧法师是主法,在大殿上领众礼佛绕念。他披着袈裟,微微躬着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走,整个大殿显得庄严肃穆。后来年高体弱,行动不便之时,他还请侍者搀扶着领众绕佛,实在走不动时,就倚着大殿的柱子稍息一会。国清寺住持可明大和尚及全寺执事多次劝他不必随众,而他仍然一如既往。
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法事,净慧法师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就是放蒙山。 放蒙山即蒙山施食,通过诵蒙山施食文、持诵真言,运心作观,施食于鬼神、饿鬼等六道众生。他曾发愿:只要住世一天,就要主持放一堂蒙山与六道众生结缘。净慧法师每天晚上坚持在妙法堂放蒙山,领众唱诵经文。有时候,他为了培养后学,就放手让弟子领唱,自己在那里打坐了。放一堂蒙山需要两个小时,侍者们见他一直纹丝不动,以为他坐化了,很惊慌地上去一看,才发现老和尚是入定了。叮一声引磬,又回娑婆世界。
净慧法师大慈大悲,他的平等理念和忍辱功夫一直为人称道。他视一切众生为佛,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一样地礼敬和关切。在他晚年时,他的声望日隆,前来皈依的四方弟子数以万计。每天都有一批批纷至沓来的信众拜访他,他有求必应,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虚弱,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接待。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无论你是带着礼物还是空手而来,他一视同仁,一样地劝你戒杀、念佛、放生,多行善事。临别时,一样地要回赠你一袋佛书,让你学佛,一些糕点水果,让你在路途中充饥解渴。
净慧法师对每个人都恭敬有礼,每经一事,必向人口念阿弥陀佛,合掌致意。令人称奇的是,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徒弟,他都恭敬合掌,并以法师尊称。
皈依弟子数以万计,见有来访者,必劝以戒杀、念佛、放生,多行善事。毕生严以律己,生活清苦,凡有供养多用于弘化慈善之事。
净慧系浙江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台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001年12月30日16时30分(阿弥陀佛圣诞前一天),法师于天台山国清寺安详示寂,世寿八十六,法腊七十二。往生后坐在佛龛里,整个身体缩得很小,头泛着亮光,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像活人一样。老法师肉身入塔,灵塔立于寺前山。
在老法师的追悼回向法会上,成千上万的四方信众和弟子都赶赴台宗祖庭国清寺为老法师送行。国清寺住持可明大和尚在悼词中说:今天,我们会聚一堂,深切悼念德高望重的净慧老法师,缅怀他一生为弘扬天台教观,对天台山佛教及至中国佛教天台宗所作的不朽业绩。浙江省佛教协会的一幅挽联高度概括了净慧老法师的一生贡献:利生为事业功归社会,弘法是家务望重宗门。
净慧法师教依天台,行归净土,坚持弘宗演教、台净双修。他的一生,就是修行证道,弘法济世的一生。他从16岁进国清寺受具足戒,至86岁舍报西归,这70年间除了赴北京中国佛学院深造3年外,几乎是足不出山门,每天青灯黄卷,晨昏苦切,以证佛道。在中国佛教界,国清寺净慧法师的德行是有口皆碑的。
传喜法师讲净慧老法师的修为:
师父(悟道老和尚)后来才秘密地跟我说,他以前曾和净慧老法师,在静权老法师那里做侍者,做了十几年。净慧老法师三十多岁就证得了念佛三昧。证得念佛三昧有什么瑞相吗?我们常人晚上看不到东西,伸手不见五指。证得念佛三昧,可以看到一片红光充满世界,整个宇宙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在密宗里是红光,显宗修道证道的,也可以证到红光。
净慧老法师跟我师父说:我想往生了,我想去极乐世界了。师父就跟他说:不可以走。你要留在这个世界,和众生结缘,带有缘众生一起往生。那个时候净慧老法师只有30多岁,就证得了。为什么?他们在师父身边兢兢业业,夜不倒单,日中一食。我们师父托钵日中一食18年,诵《妙法莲华经》3000多部,其他经典还有很多。他们这些和尚,我看这个世界上,好像都不知道他们是宝贝。
净慧老法师年纪还没到70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国清寺走路,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就打他一大嘴巴子,打完了指着老法师鼻子骂:你这个出家人,为什么要带走我老婆?!净慧老法师被人打了,很多人都围着看。老法师看着那个人笑笑,念了句阿弥陀佛,说:你啊!有没有看错人啊!有时候这是化现。不通过他来打,别人不知道这个老法师功夫有多深。这个人一看,认错了,赶快跪下来磕头忏悔: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事情传出来,大家知道,这个老和尚功夫非常了得。这是我在师父身边才能听到的故事。
他早早就证得了念佛三昧,他一直不出山门60多年。到60岁,才开始收皈依弟子。结果收了好几十万,86岁的时候,坐在那里安详往生。不单密宗里面,修得人可以缩小,在显宗里我也看到了,这就是净慧老法师。他圆寂的时候,身体缩得很小,头缩得很小,但是非常光亮,像活人一样,坐在龛里面。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我也在。
通过接触这些,看到他们这些老法师,炉火纯青的道力,却没有人去欣赏,没有人知道。佛法这么殊胜,我们人生就在生灭里面转,不生不灭的殊胜佛法不懂,可惜啊!这时候我真的想出家了。为什么?圣教衰弱,众生在苦海里,光光自己流泪还不行,还要让大家都流泪,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按:所谓红光者即非红光是名红光,不必执着。【page】
明海法师追忆净慧长老: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师父(净慧老和尚)的情景:一位老和尚从书桌上抬起头,从容地转过身,慈悲安详,和蔼可亲。因为是冬天,他还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我好奇地想:怎么和尚还戴帽子呢?我这样才一动念,师父就随手把帽子摘下来。我想:这老和尚一定有神通呢!
后来师父淡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神通。对他这话我总不信,便用心观察,神通虽然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妙处。
师父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三间相通的房子,中间一间是佛堂兼客厅,边上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日常每在这里工作,如果有人拜访,一转身又可以接待客人。
师父的工作都要伏案去做:写文章、改文章、校对稿样、给信徒回信,他做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字迹从不潦草,标点符号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帮忙誊一份东西,他看了指出许多毛病:破折号应在两格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句号、逗号在方格左下角我听了惭愧万分,平时还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过了关呢!
我曾经想:做许多工作都和修行用功不妨碍,做师父这份案头工作却不好用功。你想:一边写文章,一边念佛或者观心,那是不行的,文章一定写不出来。有一次我拿这样的问题问师父,他说:看书就看书,写文章就写文章,一心一意,不起杂念,这就是修行。
这话很平淡,我却做不到,难就难在一心一意上。我的习惯,每每写文章时惦记着打坐,打坐时又老想着文章该怎么写。总之是心里总有一些和身口不相应的细微妄想流动,走路时不安心走路,吃饭时不安心吃饭,所谓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在哪里呢?自己都觉察不出。
师父却总是那样专注,写文章是这样,吃饭是这样,扫地是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平常的:早起坐禅、扫地、打开水、到斋堂打饭、坐办公室、改稿、校稿。理论起来可以说是弘法度众生,师父做起来却是如此平实、安详,本地风光、自自然然。他扫地时是那样从容不迫,心无旁骛,仿佛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要我们学会扫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无有间断,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成就大的道业,就能振作佛法的教运
当然,师父要是有条件一直专注于案头工作也好,事实是他的工作经常被前来拜访的信徒打断。有的是修行遇到问题要请教,也有的刚接触佛教,还有的是工作、生活不顺心,请师父解忧。来的人有学生、工人,有家庭妇女,有时一家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
这时候,师父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这些来访者。和他们讲佛法、聊家常、解答疑难,话语从容平实,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人们围着他,像冬天里围着一盆火,舍不得离开。
等来访者一走,师父又回到书桌旁,拿起了笔。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终于感觉到:师父如是的行持中大有文章在。首先我自己做不到。换了我,写文章到精彩处,有人打断,心里会生烦恼;而谈话结束后,心又不容易收回,一定还挂记着刚才的谈话。师父却两无妨碍,他放下案头的书、笔,接待来客,给人的印象他刚才什么都没干,专门等你来拜访呢,所 以才那样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等人一走,他又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一直如此,没有中断。
此中有真意。我揣摩了很长时间,后来师父说:要活在当下。我才有点恍然了。活在当下,也就是斩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而安住于现前清净明觉的一念。这种安住等于无住。因为就此当下一念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成为永恒。
《华严经》上说: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际我皆入。这个入于三世的一念既在三世中又在三世外,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卖点心的婆子喝问德山要点哪个心时,德山就被束缚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囚笼里而打失了当下一念。
活在当下,也就是安心于当下。能安心于当下也就能安心于时时处处。古代的禅德饥来吃饭困来眠,无处青山不道场,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因为总能活在当下,所以他总显得那样自在洒脱,处理问题应付裕如,不费一些思索,纯为现时境界。不管是作文还是讲开示他都是信手拈来,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上所说的定慧等持吧。
我有不爱整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过去长期的学生生活养成的,师父几次批评我,我却进步不大。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师父则不然,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他走到哪里就把清洁和秩序带到哪里。他常给我念叨:虚云老和尚了不起,虽然行头陀行、穿百衲,但他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案头、禅榻总是整齐洁净的。
起初,对他的话我一直漠然淡然,后来才慢慢领会:这也是修行。
柏林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历史的风暴却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只有几棵古柏、一座佛塔还使人能依稀辨出这是一座古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师父成了设计师。这儿修什么,那儿建什么,全部都由他亲自擘划,所有工程的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意见。有时他带着我们在寺里四处巡视,向我们描述他的复兴蓝图,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每次回寺,即使是深夜,他也要去查看建筑工程的进展,有时冷不丁他就会挑出毛病,使承包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
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愍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已来,多四大海水。
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 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 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13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